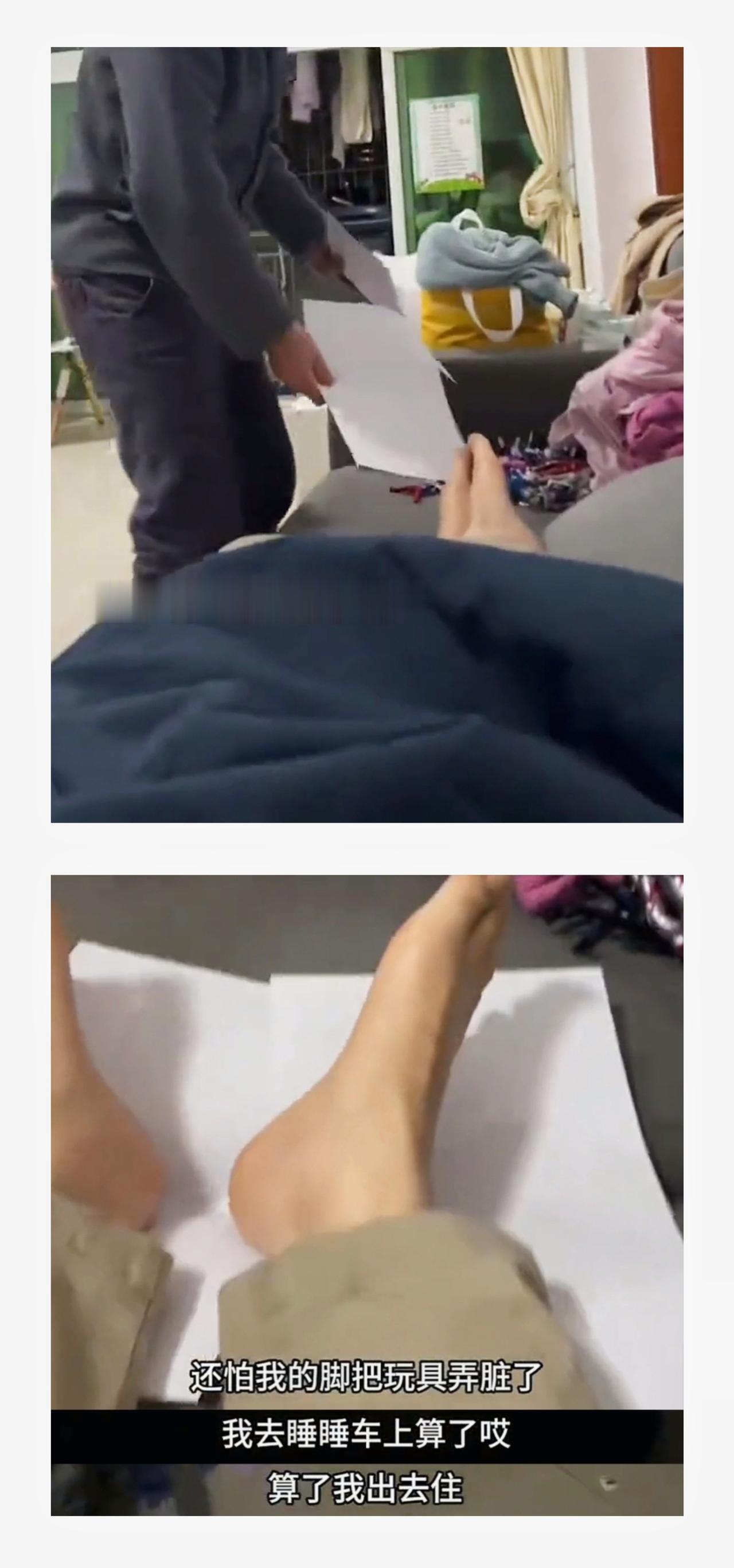1939年,白求恩被埋葬在河北唐县,由于他在前线战死,交通队只好秘密的把白求恩的尸体伪装成一个重伤的人,然后连夜赶路,将他送到了后方的于家寨。 山风卷着碎雪打在脸上,像小石子砸得生疼,交通队的老周攥着担架杆的手冻得通红,指节都泛了白。担架上的白求恩大夫盖着厚厚的棉被,只露出半张脸,呼吸早就停了,可老周总觉得能听见他之前在手术台前的声音——上个月老周被弹片划伤肚子,就是白大夫在山坳里的破庙里给他做的手术,当时庙顶的瓦片被炮弹震得哗哗掉,白大夫头也不抬地说“别紧张,我给你把弹片取出来,你还得回去打鬼子呢”。 走到山口的敌人岗哨时,老周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岗哨的探照灯扫过来,队长赶紧迎上去,把怀里揣的半袋粗粮饼递过去:“老总,这是我们队里的重伤员,洋大夫,打鬼子受了伤,再耽误就没命了。”敌人掀开被子一角,瞅了瞅白求恩高鼻梁的脸,又捏了捏粗粮饼,骂骂咧咧地挥挥手:“赶紧滚!别在这儿碍眼!” 大家不敢多停,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于家寨赶,担架的木杆压得咯吱直响,只有雪粒子落在棉袄上的沙沙声。天刚蒙蒙亮,村头的老支书已经攥着个热红薯在等了,他把大家让进屋里,灶台上的铁锅冒着热气,锅里熬着稀粥。 老周帮着把白大夫的遗体轻轻放在土炕上,老支书从柜子里翻出件干净的粗布军装,那是他儿子参军时留下的,一直舍不得穿。村里的王婶端来一盆温水,轻轻给白大夫擦了擦脸,又把自己刚编的野菊花花环放在他枕边。 后山的向阳坡上,大家悄悄挖了个坑,把白大夫埋了,老周在墓前插了根从山上折的红松枝。风停了,阳光透过树枝洒下来,落在松枝上,像给它镀了层暖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