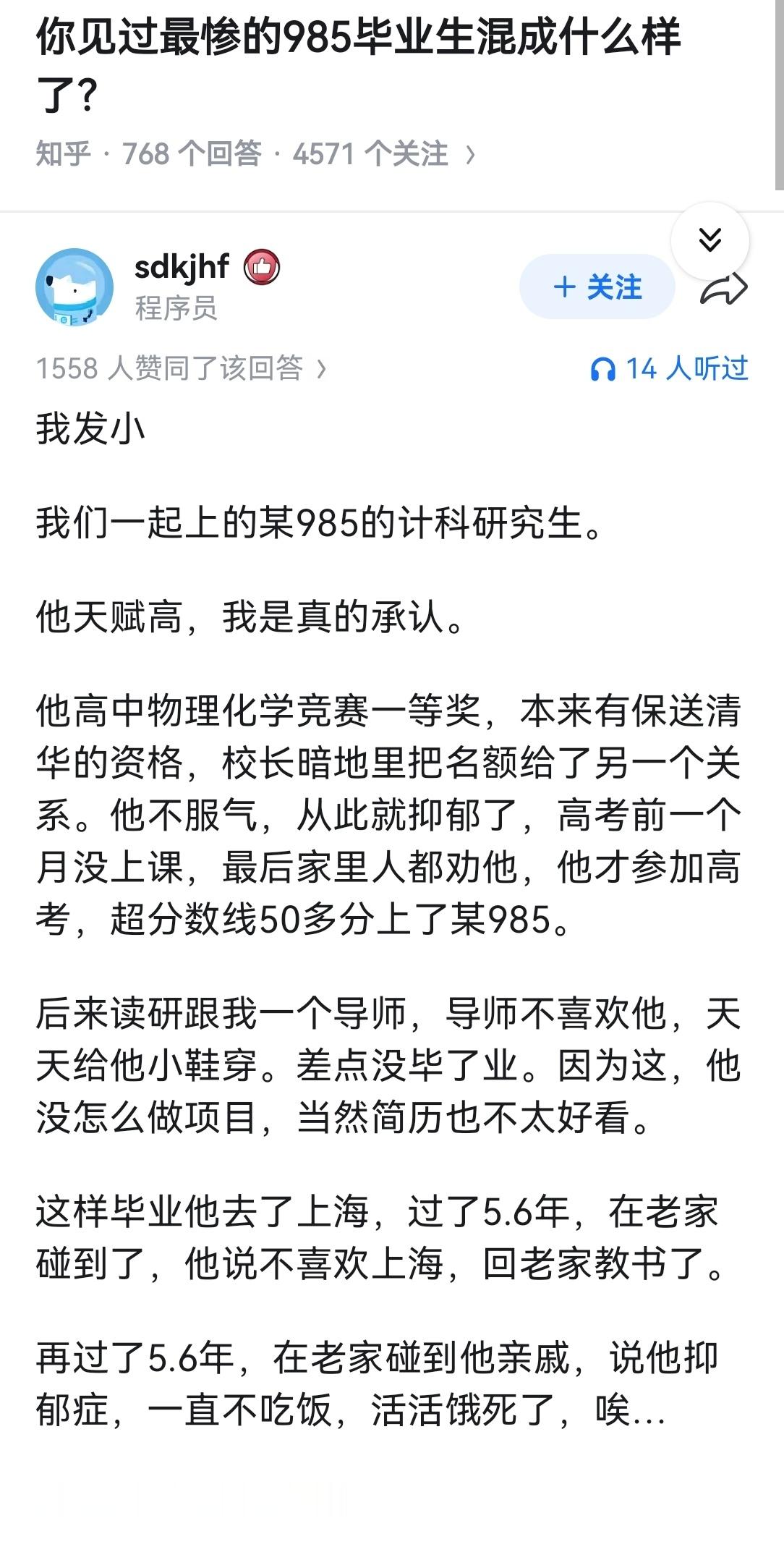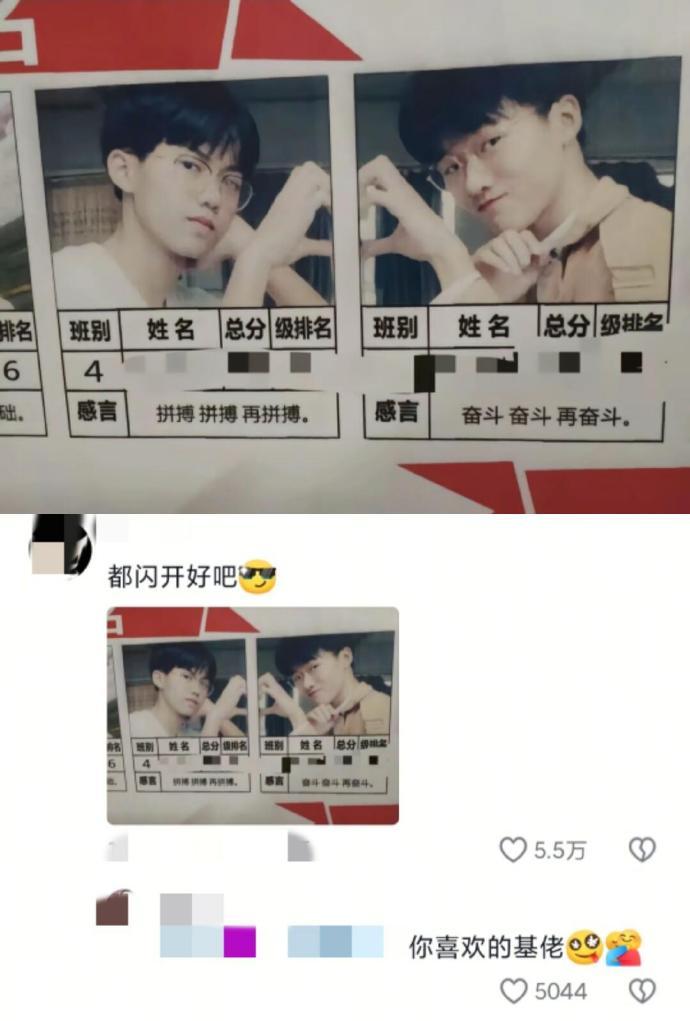1988年,教师家庭的23岁的女儿被保送清华。旅游途中,她爱上35岁的酒厂工人,非要结婚。教授苦口婆心劝说:学历太低了!女儿:“嫁给他,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1988年底,杭州西子湖畔,一位老教师拿着雨伞站在院子里,不说话。他盯着手里的信,是女儿从西北某旅游城市寄回来的,上面只有一句话:“爸,我决定了,我要嫁他。” 身边的老伴劝他坐下,他却坐不住。“那人是干啥的?她说,他是工人,我说,工人怎么了?工人我尊敬。但是,她是咱家的独生女啊,一个从小读书读到清华硕士的姑娘,怎么就看上一个啤酒厂工人了?” 这句话成了那个年头不少家庭的日常慨叹,那时人人图的是“门当户对”四个字。 清华硕士姑娘和一个中专学历的技术员,怎么看都称不上是门当户对。 可成婚这事,从来不光凭纸上的功课。 一趟春游列车,一段命运错位的相遇,就这么压下了所有“合适”两个字。 1989年4月28日,一列开往济南的绿皮火车闷声慢跑。四月份的天还冷,车厢里却热得人喘不过气。 陈薇,一个即将保送清华生化系的23岁姑娘,双手抱着一本厚厚的英文教材,站在走道边被人挤得前胸贴后背。 硬座上,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腾出了自己的座位,顺手把自己的书摊在小桌上:“坐吧,反正我也站得惯。” 姑娘犹豫了一下,谢过他落座,顺带一眼扫了过去,书名是《管理的第一课》。 她心里一挑眉,这不是酒厂工人该读的书。 长达六小时的车程,他们聊了从啤酒的发酵工序聊到能源政策,旁人听着都觉得怪,像对研究生和夜校生在切磋“平流层里的愿景”。 她问:“你学历是?” 他擦了擦额头,说:“中专,青岛技校,发酵专业。” 说这话时他语气平稳,脸上也不自卑。她反而愣住了。 那年头,学历差距如天堑。可他不卑,甚至连她的专业,他也略懂个大概,还能提两句人话。 火车开到济南,两人没再说话。他把她的书包递回来,“我的电话写在里头夹页里,别碍事。” 接下来的日子像是命中有约。三个月后,他第一次带她进啤酒厂,她戴着帽子,站在发酵车间里一边闻一边皱眉说:“怪臭的。” 他笑,说:“习惯了,这味是挣钱的味儿。” 到她鼓起勇气告诉父母这事时,家里炸了。母亲几乎要晕过去,父亲则不怒,而是更深的痛惜。 “你是我们一生的心血,你怎么能不计前后,嫁一个厂里的工人?” 姑娘顶着哭红的眼说:“爸,我现在能决定自己要什么,我不是嫁学历,我是嫁这个人。” 她不说别的,只说,她躲在他身后,有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而她那些让人耳鸣的课题和实验,他一句不懂,却每次都能陪她走完全程。 1990年年底,麻一铭辞去了青岛啤酒厂的稳定工作,只身北上。他说:“她在哪儿,我在哪儿。” 当时单位还破天荒地挽留:“你留下,我们帮你解决家属工作。”他却只是笑笑,说:“谢了人事科,我该到北京陪家了。” 北漂那会,他住在石景山一个漏风的平房里,打过工地,也领过打零工日薪。 家里没有暖气,他烧炭自己做饭,还写笔记。笔记的内容从管理会计,到预算分析,越看越不像工人。 他的目标明了:让妻子安心科研,自己的存在,必须是减重而不是加码。 当别人买电视攒彩电,他拿钱给她报了英文期刊的订阅费。她回家看到信封的时候,愣了半分钟,然后默默把饭加了个菜。 1992年,陈薇面前摊开两个offer:一个是外企年薪优渥,一个是从事军事医学的科研单位,待遇微薄,还可能入军籍。 她犹豫。麻一铭看着她,一字一句说:“你想做啥就做啥,家里有我。” 那天,她没说谢谢,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走进了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大门,从此没有回头。 后面的故事,大家或许听过一部分,2003年非典,她在实验室连续几个月不出门,儿子问:“妈妈去哪了?”麻一铭蹲下来,把孩子领到窗前:“妈妈在打怪兽,等打完了就回来。” 他自己则每天做饭,为老人送药,每一件小事都像在跟紧急时局赛跑。 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发,她跟队去西非。他没有追问,只悄悄地开始查资料、问同行,“那边天气怎么样?她吃不吃得惯?” 他在电话里轻描淡写地说着这些琐事,每一句背后都是“我理解你,又守得住你。” 2020年春,她赴武汉,封城113天。他看着屏幕里她的头发一天比一天白,眼角挂着泪,却一声不吭。他知道,她不能回头,他就必须站稳。 清华和中专,一个是科研尖兵,一个是“家庭煮夫”,他们看起来并不相配,但却也从不分离。 也许在别人眼中,她嫁得委屈;可在她眼里,他才是那个“能让我踏实走进每一个战场的人”。 一段婚姻,再热烈不过三五年;能推着彼此不断迈向前方的,是沉默里的支撑,是凡俗日子里的并肩。 他不是科学家,却用一辈子守护了一个人民英雄的征途。 信息来源:陈薇哭了!她被丈夫宠爱30年的"神仙爱情",才是真的甜到齁!——南宁女性 2020-09-12 1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