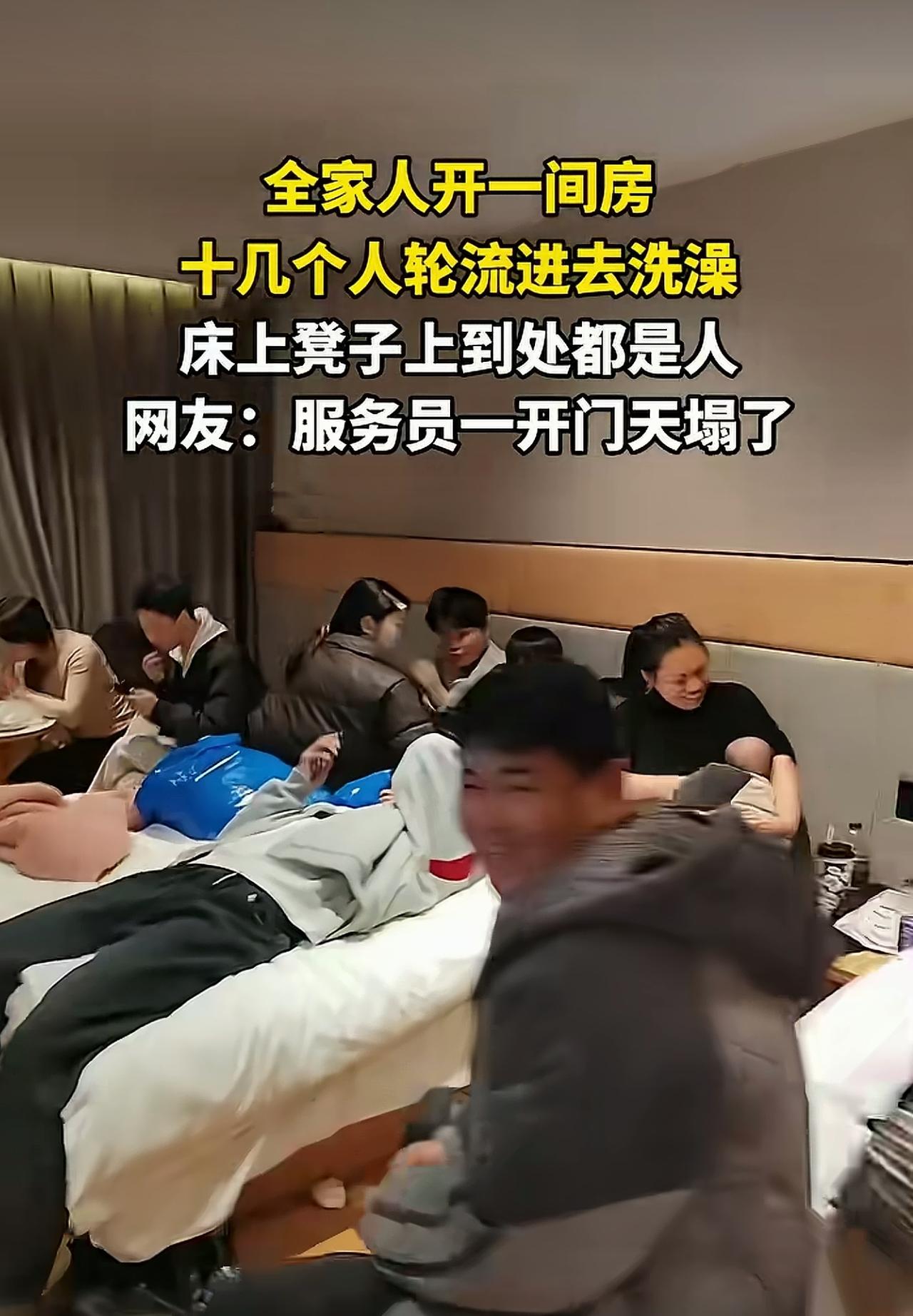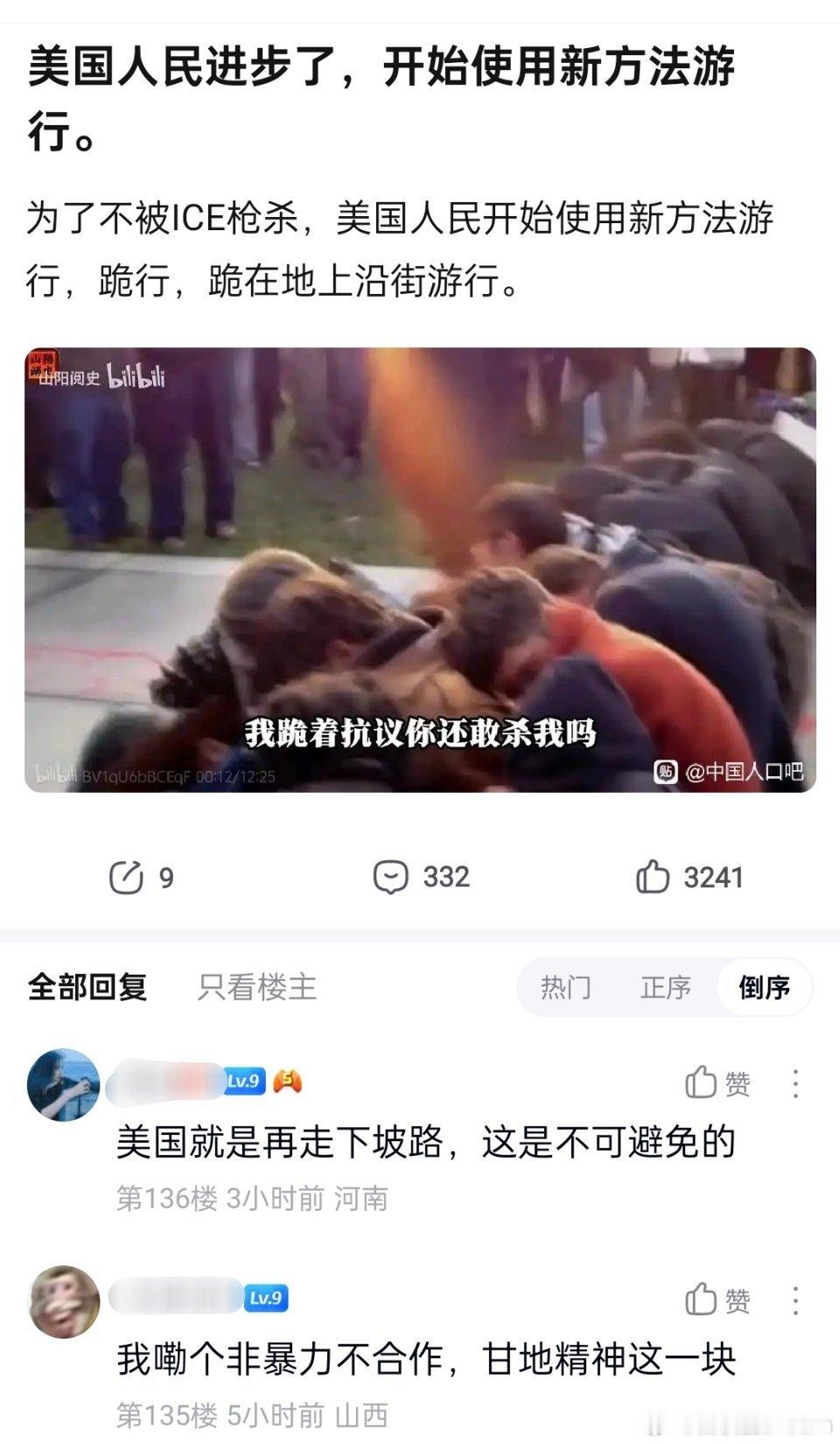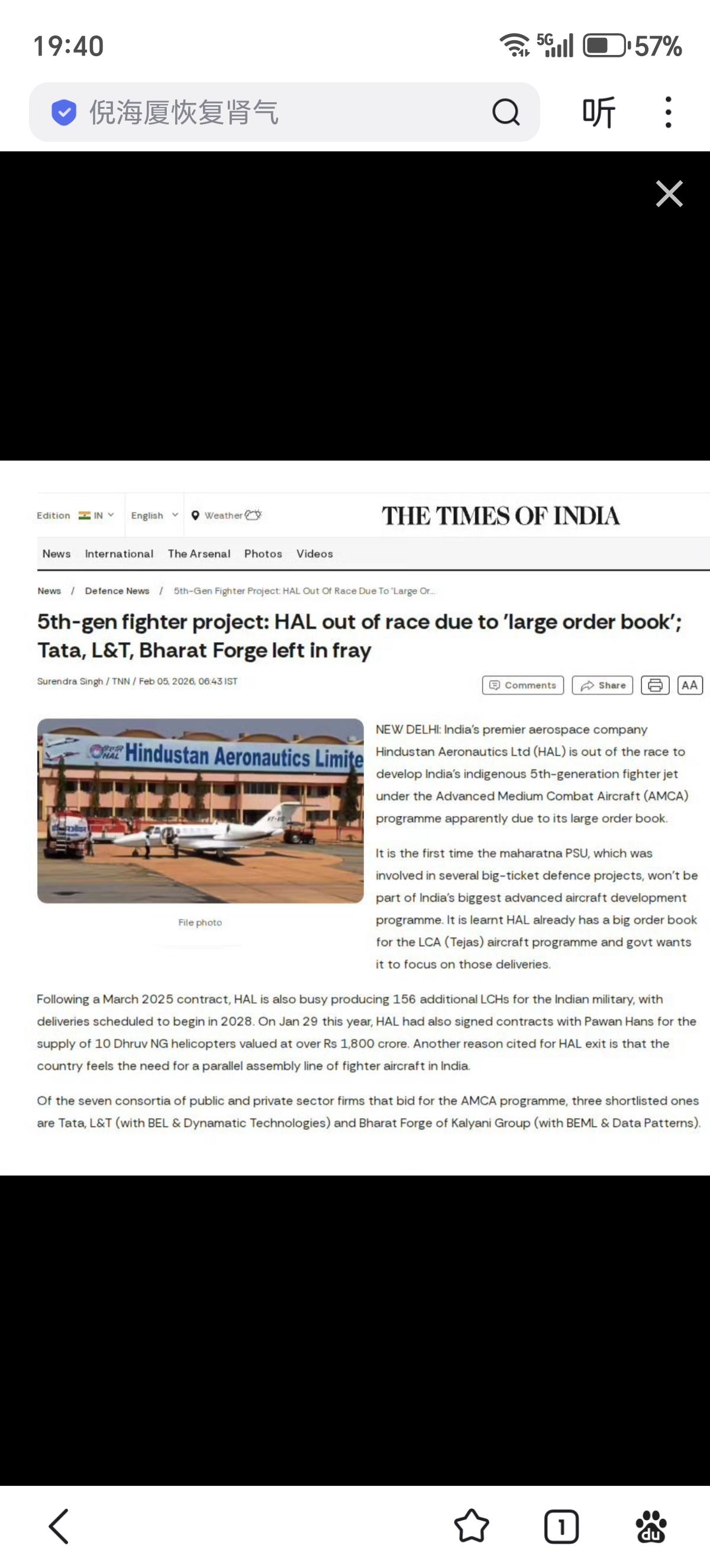唐·德里罗是美国20世纪下半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白噪音》《地下世界》《大都会》《欧米茄点》《坠落的人》《天秤星座》等等。
《白噪音》《白噪音》发表于1985年,是唐·德里罗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不仅是他的声名鹊起之作,也是美国后现代文学最具经典性的代表之作。

《白噪音》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中西部一个名为“铁匠镇”的大学城。主人公杰克·格拉迪尼是该校“希特勒研究系”的系主任,与第四任妻子芭比特及一群来自前几段婚姻的孩子,组成一个典型的后现代混合家庭。小说开篇描绘的大学新生入学场景,并非充满朝气与希望,而是被琳琅满目的商品、保养得宜却神情空洞的父母,以及一种仪式般的物质堆砌所充斥。这个家庭生活的核心场景,往往是全家人聚集在电视机前,让各种节目的声浪——新闻、广告、情景喜剧——如同背景“白噪音”般填满空间的每一处缝隙。
德里罗精妙地捕捉了消费主义如何成为新宗教。格拉迪尼一家定期前往大型超市的购物之旅,宛如一场朝圣。超市里整齐划一、色彩鲜艳的商品阵列,营造出一种丰裕与秩序的幻象,购买行为本身成为抵御虚无、确认存在的方式。然而,这种消费带来的满足转瞬即逝,需要被下一次购买不断填补。与此同时,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无孔不入,它们不仅提供信息,更在深层次上塑造着人们的认知、欲望乃至对现实的感知。真实与虚拟的边界在持续的声波与图像轰炸中变得模糊,技术不再仅仅是工具,它已成为一种环境,一种氛围,一种决定生活节奏与内容的无形架构。小说第一部分的标题“电波与辐射”,早已隐喻了这种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渗透与控制。

小说的叙事转折点,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生态危机——一起名为“尼奥丁衍生物”的工业化学毒气泄漏事故,一团“空中毒雾”威胁着铁匠镇。当局仓促组织撤离,整个社群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与混乱。德里罗以近乎纪实的手法,描绘了这场现代版的“出埃及记”:汽车排起长龙,谣言四起,官方信息矛盾且迟缓,每个人都暴露在不可见、不可知的风险之中。
主人公杰克在撤离途中,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而在毒雾中暴露了短短两分半钟。正是这短暂的暴露,给他“体内植入了死亡”。这一情节极具象征意义:现代工业文明所创造的风险是抽象的、延迟的、内在的,它不像传统危险那样即刻可见。死亡以分子形式潜入身体,转化为一种持续的心理煎熬——对癌症的恐惧,对统计学概率的计算,对生命倒计时的病态感知。“空中毒物事件”不仅污染了环境,更深层地毒害了人的心灵,制造了一种普遍的、弥漫性的生存性焦虑。技术本许诺带来安全与掌控,此刻却暴露出其自身的失控与反噬,揭示了人类在自身创造的“超客体”(超越人类控制范围的复杂技术系统)面前的脆弱与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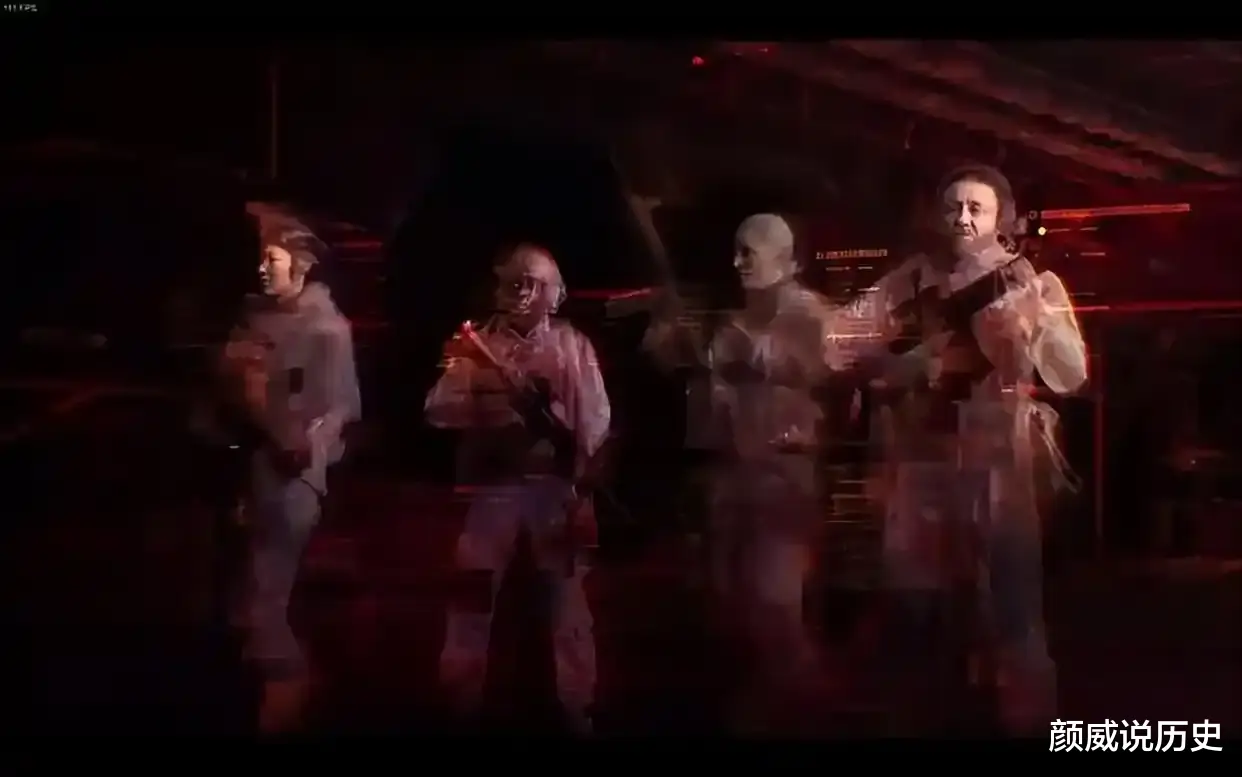
死亡的阴影驱使杰克走向小说的第三幕,也是最具戏剧冲突的部分——“‘戴乐儿’闹剧”。杰克得知,妻子芭比特为了获取一种名为“戴乐儿”的试验性药物(声称能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曾与该项目的研究者格雷先生发生关系。愤怒、羞辱与自身对死亡的深切恐惧交织在一起,促使杰克策划了一场漏洞百出的复仇。他试图谋杀格雷,抢夺“戴乐儿”。
这场“闹剧”以彻底的失败告终:计划笨拙,过程狼狈,结果荒诞。杰克非但没有成功复仇或获得神药,反而让自己更深地陷入暴力、罪恶与滑稽的境地。德里罗通过这出闹剧表明,在技术理性无法解决终极的死亡问题时,人们可能转向非理性的、甚至暴力的方式来寻求解脱,但最终找到的只是更大的虚无与混乱。“戴乐儿”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它代表技术社会许诺的又一虚假解药——用化学物质来解决形而上的存在主义危机,其结果只能是更深的异化。

《白噪音》的主要命题,在于揭示技术如何从为人服务的工具,演变为统治人类的“新君主”。在德里罗描绘的世界里,技术已形成一张巨网:
日常生活的全面殖民:从家用电器到媒体设备,从医疗检查到食品工业,技术细节构成了日常经验的基底,人们无意识地依赖并遵循其逻辑。
认知与情感的塑造:大众媒介持续输出标准化的图像、叙事和价值观,钝化个人的批判性思维,培育被动的接受与消费心态。

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在“空中毒物事件”中,技术系统制造了危机,而官僚与技术专家系统则试图管理危机。信息被管控,解释权被垄断,民众在庞大的技术-官僚机器面前,只能沦为被疏散、被检测、被统计的对象,主体性丧失殆尽。
当这种技术统治与资本利益、官僚权力紧密结合时,便诞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更高效也更隐蔽的专制形式。它不依赖显而易见的暴力,而是通过制造依赖、管理风险、提供舒适幻象来消解反抗的意志。正如小说所暗示,真正的极权主义可能就藏身于超市的荧光灯下、电视的雪花屏里,以及那些承诺让我们“活得更好、恐惧更少”的科技福音之中。
技术的异化力量不仅作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深刻地腐蚀着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在《白噪音》描绘的社会图景中:

关系的原子化:格拉迪尼的家庭成员虽然物理上共处一室,但精神上各自沉浸在媒体流或个人焦虑中。交流常被电视台词或消费话题填满,缺乏深度的情感沟通。
灾难面前的冷漠:“空中毒物事件”中,恐慌是自私的。人们只关心自身及核心家庭的安危,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甚至将灾难现场视为某种奇观。社会团结在生存威胁下迅速蒸发。
死亡的私人化与商品化:对死亡的恐惧成为最私密也最普遍的焦虑。人们不再在宗教或哲学共同体中寻求慰藉,而是试图通过消费或知识来个人化地处理它。这反而加深了孤独。

同情心的消逝:在一个被技术中介、风险计算和自我保存逻辑主导的世界里,传统的人性纽带——关爱、同情、无私的奉献——显得陈旧而无力。社会生态沦为一片精神的荒漠,每个人都是恐惧的孤岛。
唐·德里罗通过这部小说,向我们发出了一声尖锐而持久的警告:文明的进步若失去人文价值的导航,技术的飞跃若缺乏对生命本质的深思,便可能将我们带入一个物质丰裕却精神贫瘠、互联互通却心灵隔绝、追求永生却时刻被死亡恐惧追逐的荒诞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