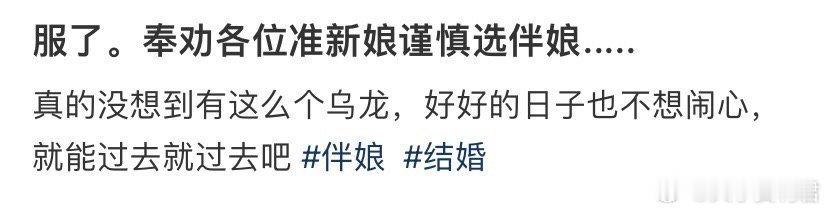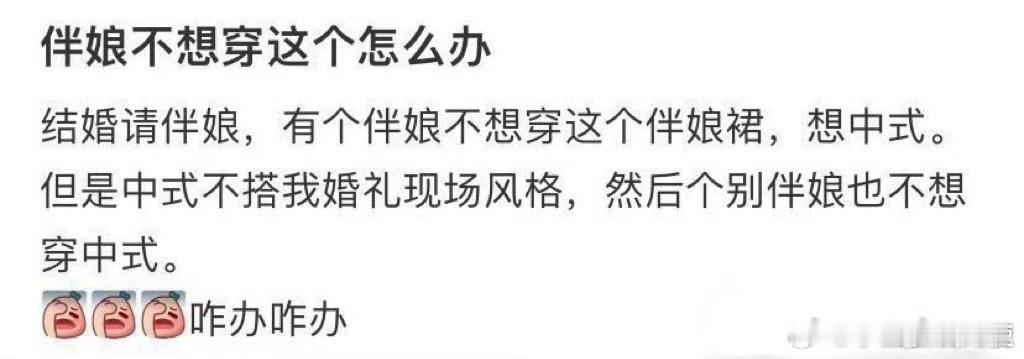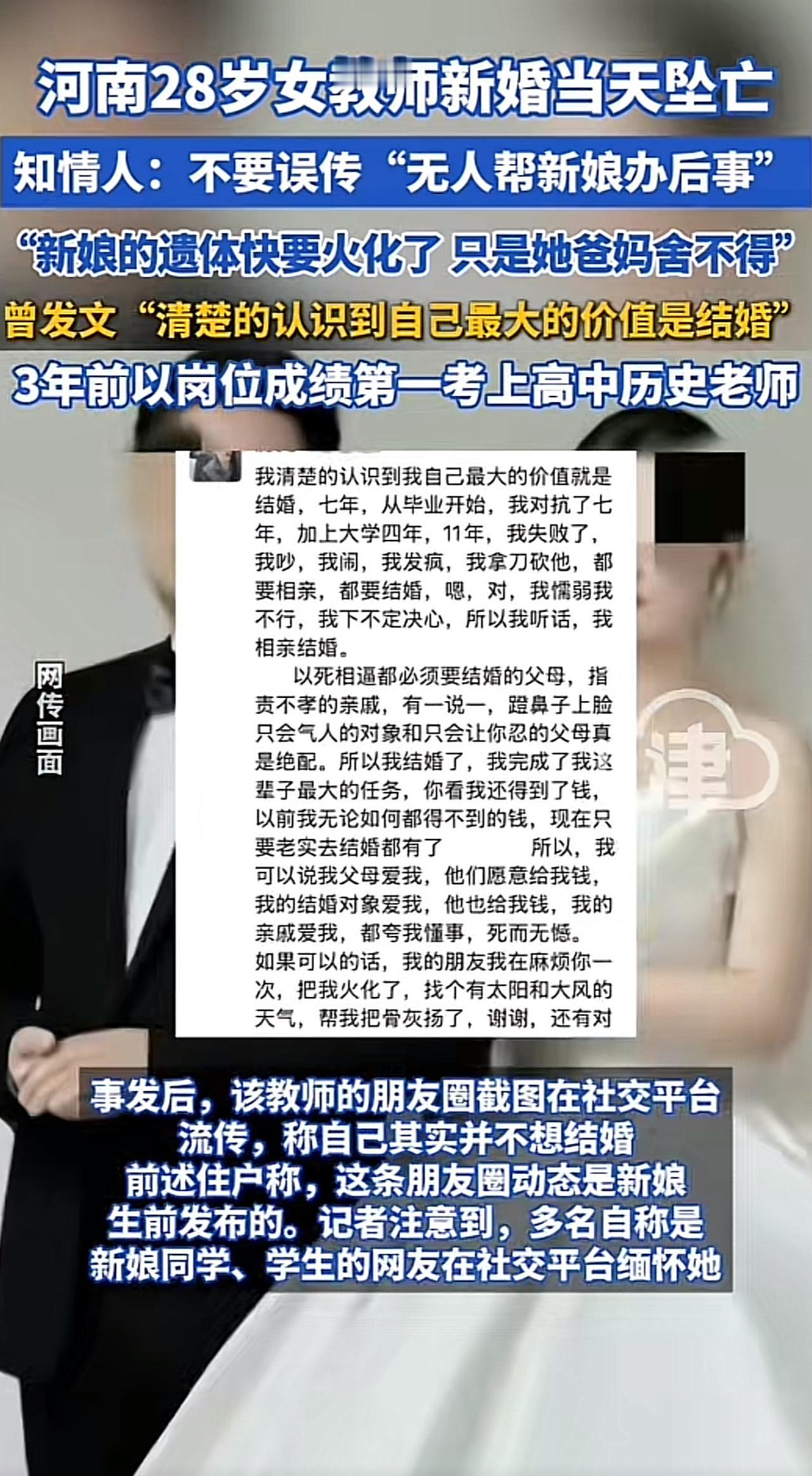婚礼当天,同样装穷的男友,见台上我以千金身份出席,瞬间如遭雷击。台下第三排的椅子被他攥得咯吱响,手里那束他凌晨三点去花市挑的向日葵,花瓣都被捏皱了。司仪喊了三遍“请新郎上台”,他像钉在原地,眼睛直勾勾盯着台上穿定制婚纱的人——昨天还跟他挤在出租屋小沙发上,分一碗泡面的女朋友,怎么就成了财经杂志封面上那个林氏集团的继承人? 婚礼进行曲响到第三小节时,我看见他站在台下第三排。 不是该并肩站在台上的位置,是观众席里最普通的那个角落。 他穿的还是昨天跟我挤出租屋时那件洗得起球的白衬衫,袖口卷了三圈,露出手腕上磨掉色的电子表——那是我们刚在一起时,他用兼职工资买的情侣款,我的那块早就被我妈收进首饰盒最底层了。 手里的向日葵是凌晨三点的花市,他发微信说“挑了最像你笑起来的那束”,现在花瓣被他捏得卷了边,金黄色的花粉蹭在他手背上,像谁不小心撒了把碎金。 司仪的声音透过音响撞过来:“请新郎上台。” 他没动。 “请新郎上台。” 他还是没动,眼睛直勾勾盯着台上,像看一个突然闯进梦里的陌生人。 台下第三排的塑料椅被他攥得咯吱响,我甚至能听见他指节用力时骨头摩擦的声音——昨天我们还在出租屋的小沙发上抢最后一口泡面,他说“你吃,我减肥”,今天我站在这里,穿着他永远买不起的定制婚纱,背后是财经杂志拍过无数次的林氏集团logo背景板。 他是不是在想,那个会为了省五块钱打车费陪他走三站路的女孩,怎么突然就成了别人嘴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林大小姐? 我看见他喉结滚了滚,手里的向日葵“啪嗒”掉在地上,花盘磕在台阶上,碎了一小瓣。 司仪第三次喊他名字时,他突然笑了,很轻的一声,像自嘲,又像终于想通了什么——原来不是同路,是我从一开始就站在岔路口,却骗他说前面是并肩的坦途。 他弯腰捡起那束皱巴巴的向日葵,转身往宴会厅后门走,白衬衫的后摆扫过椅子腿,带起一阵风。 我知道他不是不想上台,是不敢——就像他一直瞒着我,他根本不是什么“月薪五千的程序员”,他爸是跟林氏有竞争关系的张氏集团副总,他接近我,本是想打探林氏的商业机密。 我们都在装穷,他装穷是为了刺探,我装穷是为了试试,不披林氏千金的壳,能不能遇到真心。 结果呢? 他手里那束凌晨三点的向日葵,是假的真心;我昨天分他的那口泡面,是真的贪心。 他走到后门时停了一下,没回头,只是把向日葵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金黄的花瓣从桶沿漏出来,像我们这场戏里,唯一没演砸的部分。 司仪还在台上圆场:“新郎可能有点紧张……” 我对着麦克风轻轻说:“不用等了。” 台下静了两秒,然后是窃窃私语,我看见我妈脸色铁青地站起来,而出租屋那个小沙发的触感突然变得清晰——原来最舒服的不是定制婚纱的裙摆,是两个人挤着分泡面时,他胳膊蹭过我手背的温度。 可那温度,现在被我和他,一起捏碎了。 就像那束向日葵,揉皱了,就再也展不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