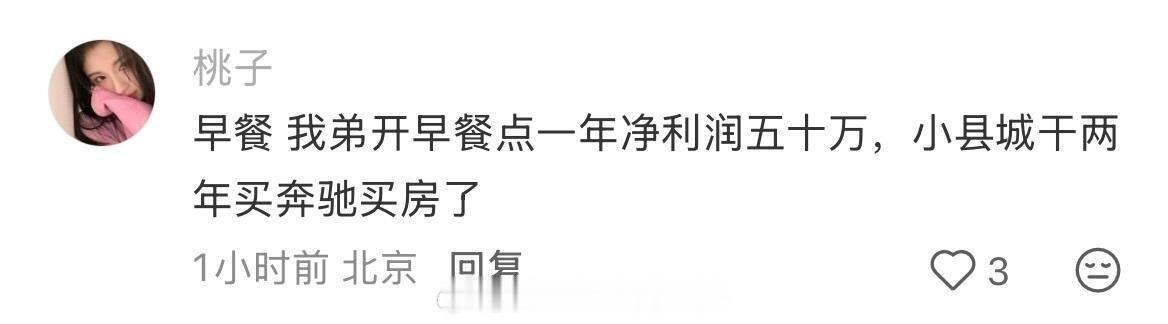1993年,一个刚做手术摘除了左眼球的老兵,大骂儿子一顿:“家里没有钱吗?你怎么还能向国家伸手呢?”病床上的纱布还渗着血,儿子捏着那张630元的医药费单据,手都在抖。 他知道父亲兜里只有卖玉米换来的几十块钱,可老兵瞪着仅存的右眼,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国家的钱要给更需要的人,咱家还能撑。” 1955年的春天,陈训杨揣着300元复员费站在公社门口时,身后的战友都以为他要盖新房。 谁也没想到,他把钱往会计桌上一拍:“买两头水牛,给队里耕田用。”剩下的零钱,给邻居家娃交了学费。 那时他左眼里的弹片还没取干净,肩膀因为扛机枪早就变了形。 四年前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他还是个被抓来的壮丁。 国民党军队里三天没吃上热饭,被俘那天,解放军炊事班端来一碗带葱花的热面条,他捧着碗,眼泪掉在面汤里。 “俺跟你们走。”就这一句话,他成了渡江突击队的一员。 1949年渡江那天,他不会水,却举着手说“俺会游”。 木船在枪林弹雨中晃得像片叶子,五小时里他来回划了六趟,把战友送过长江。 最后一趟回来,船板上全是血,300人的突击队,上岸时只剩13个能站着的。 他胳膊被弹片划开个口子,随便裹了块布,跟着部队继续追。 从云南剿匪到抗美援朝,左眼被鸟铳打穿,肩胛骨被机枪压得变了形,这些伤在他嘴里轻得像“被蚊子叮了口”。 1955年回乡后,他把军功章塞进木箱底,跟着村民下地挣工分。 队长见他肩膀不直,想给他安排轻活,他抢过最重的犁:“俺当过兵,这点力气还有。” 2019年退役军人事务部的人找到他家时,木箱里的军功章已经锈出了绿斑。 工作人员翻出那张泛黄的“水上英雄”奖状,他才慢悠悠说:“都过去了,庄稼人记那些干啥。”邻居这才知道,每天在村口拾柴的老头,当年在长江里救过那么多人。 整理他的遗物时(后来才知道他2021年走的),发现复员费账本上记着“水牛2头180元,资助李家娃学费20元”,旁边还有行小字“国家给的,该给国家用”。 如今公社的老水牛早就换成了拖拉机,但村里老人还会说,那年春天陈训杨牵来的水牛,耕出了最齐整的田垄。 他藏在箱底的军功章,和他那只空荡荡的左眼眶,都在说同一个理:真正的功勋,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是扛在肩上、种进地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