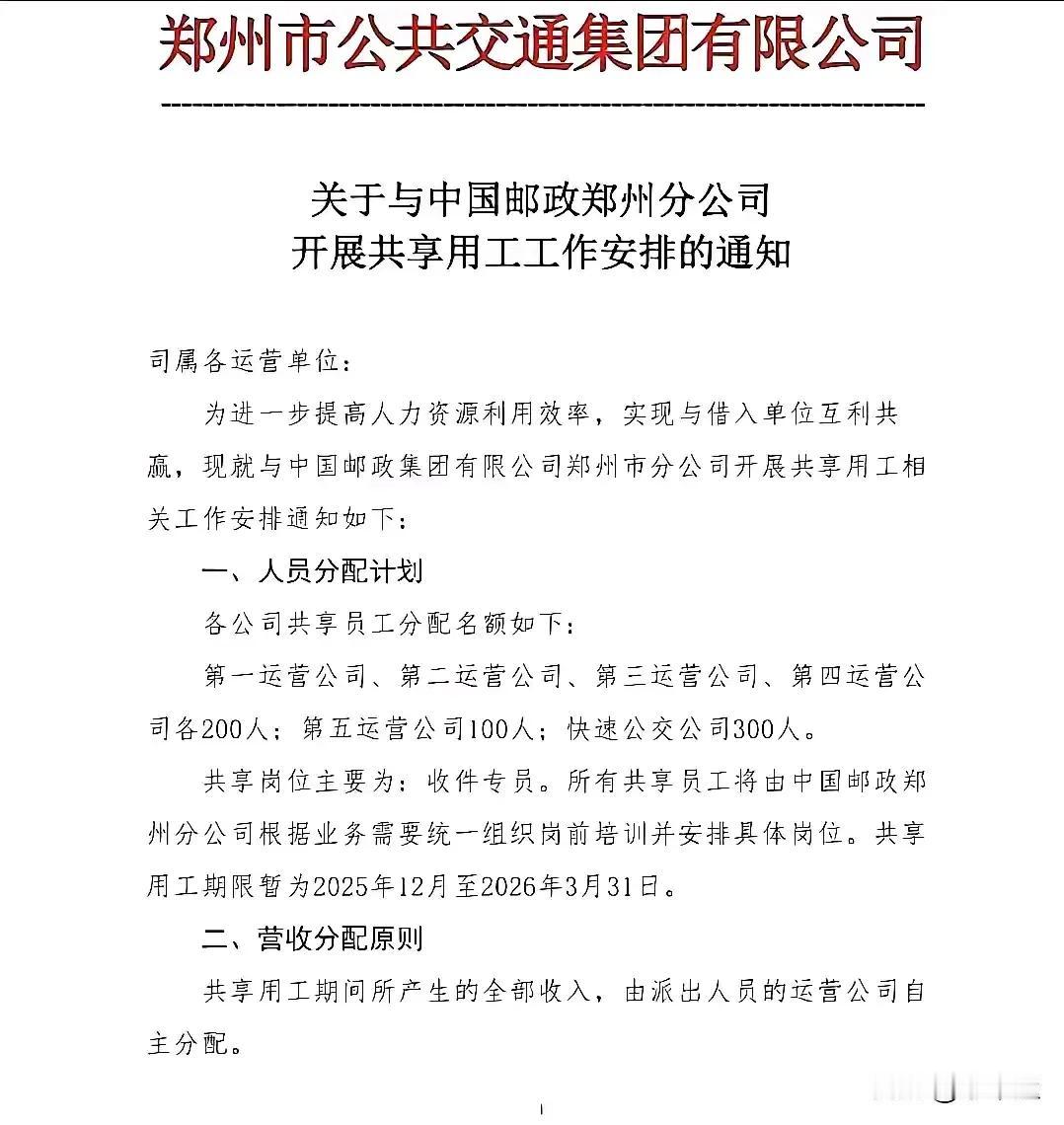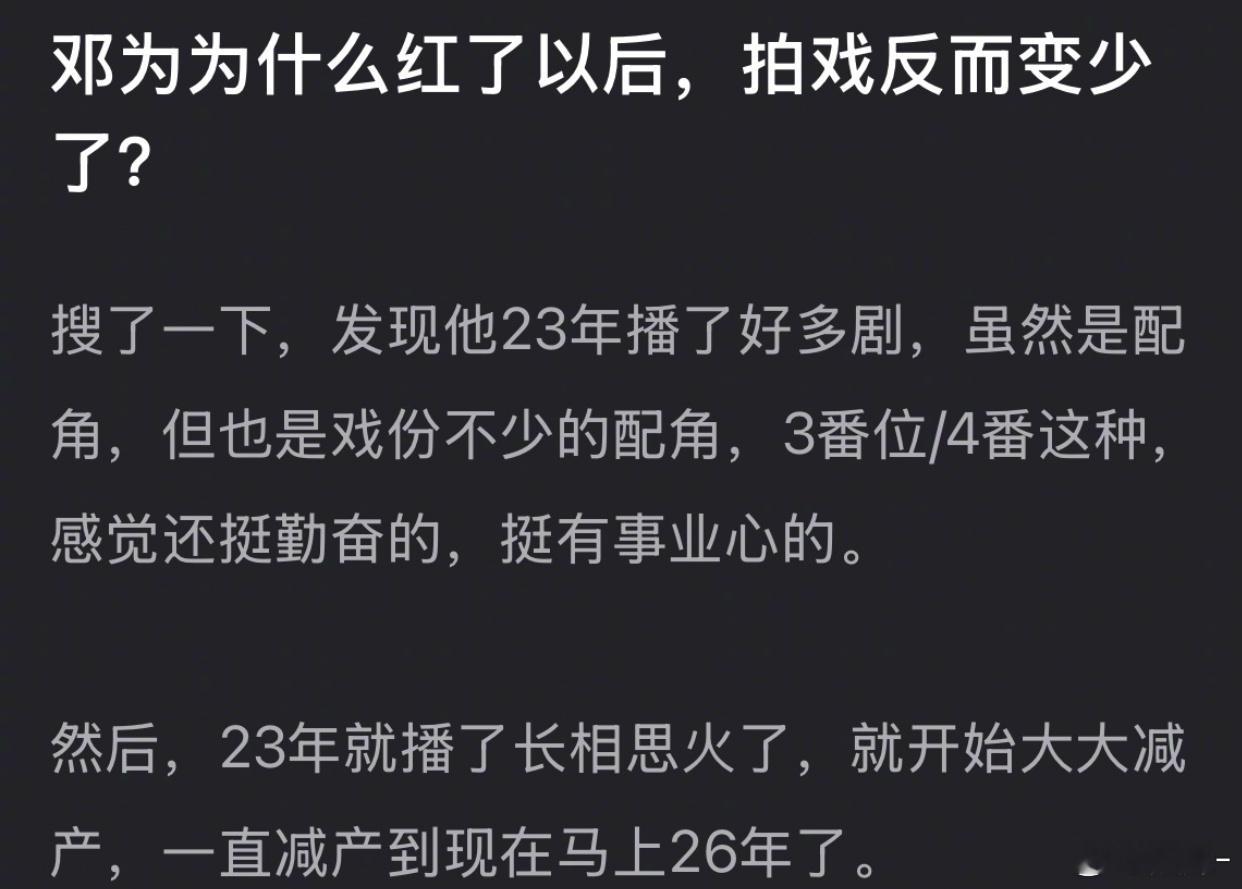我十二岁那年我奶和我二姑欺负我妈,我一杯茶水泼我二姑头上。我奶奶打我妈,我把我奶从台阶上推下来了,结果我爸把我打了一顿。那天是秋收后的第一个集日,我妈刚把晒干的玉米收进粮仓,二姑就带着我奶来了,进门就喊:“哥呢?让他出来!我听说嫂子把我上次托她买的花布私藏了?”我妈赶紧解释:“妹子,那布我给你收在衣柜里了,这就给你拿。”可二姑根本不听,伸手就把我妈手里的簸箕掀翻,玉米粒撒了一地。 十二岁那年的秋老虎还没褪尽,粮仓里新玉米的焦香混着尘土味,在院子里飘了一整天。 那天是秋收后的第一个集日,妈刚把最后一簸箕玉米粒倒进粮仓,竹簸箕的边缘还沾着几粒金黄的碎渣——她总说,粮食得一粒一粒数着疼。 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时,我正蹲在门槛上剥玉米,看见二姑挎着空篮子走在前面,奶奶拄着拐杖跟在后头,鞋跟把青石板敲得“笃笃”响。 二姑没进院就扬着嗓子喊:“哥呢?让他出来!我托嫂子买的花布,怎么听说被她私藏了?” 妈从粮仓里探出头,围裙上还沾着玉米须:“妹子,布在衣柜最底层压着呢,我这就给你取。” 她说话时,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围裙角,我看见她指节泛白——妈这辈子,跟谁说话都带着三分怯。 可二姑根本没动,突然伸手就往妈怀里的簸箕抓去,“我看是你想独吞吧!” 竹簸箕“哐当”一声翻在地上,玉米粒像断了线的珠子,滚得满院都是,有的还蹦到了奶奶的黑布鞋上;玉米粒顺着台阶缝往下滚,有的卡在砖缝里,有的滚到鸡窝边被鸡啄走,还有几粒沾在了妈掉在地上的发夹上——那是爸去年在集上给她买的,红色的塑料花儿已经磨掉了边。 我手里的玉米棒“啪嗒”掉在地上,猛地站起来冲进厨房,抓起灶台上刚沏好的热茶——那是爸早上特意给妈留的,还温着——朝着二姑后脑勺就泼了过去。 “你反了天了!”奶奶“哎哟”一声,举起拐杖就往妈背上打,“你教的好儿子!敢对长辈动手!” 拐杖带着风扫过来时,我扑过去推了奶奶一把,她往后踉跄两步,一屁股坐在了台阶上,拐杖“咕噜噜”滚到了院角。 爸是赶集回来撞见的,他刚把自行车支在院门口,看见满地玉米和坐在台阶上哭的奶奶,脸一下子就黑了。 他没问缘由,抓起门后的竹扫帚就往我身上抽,竹枝抽在胳膊上,火辣辣地疼,我咬着牙没哭,只是盯着满地乱滚的玉米粒——它们曾经那么饱满,现在却像妈掉在地上的眼泪,碎了。 可如果那天我没动手,妈是不是就要一直蹲在地上捡玉米,直到腰都直不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二姑那年秋天想给她闺女做件新棉袄,跑了三个集都没买到合适的花布,急得嘴上长了燎泡;奶奶的老寒腿一到秋收就犯,那天走了两里路来,本就一肚子火。 那天我以为自己是英雄,后来才明白,十二岁的我根本分不清“保护”和“冲动”的边界——我只看见妈红着眼圈蹲在地上捡玉米,没看见爸蹲在台阶上抽烟时,烟灰掉了满裤腿。 那天晚上,妈用热毛巾给我敷胳膊,毛巾上的热气熏得我眼睛发酸,她没说话,只是把我搂在怀里,让我听她心跳的声音。 后来二姑再也没提过花布的事,奶奶来我家时,会把拐杖轻轻放在墙根,不再敲得青石板响。 长大后才懂,有时候保护不是硬碰硬,是先看见对方眼里的难,再护住自己心里的软。 如今每次剥玉米,看见簸箕边缘沾着的碎渣,我总会想起那天满地乱滚的玉米粒——它们后来被妈一粒一粒捡回了粮仓,就像我们家那些磕磕绊绊的日子,碎了,也能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