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学历史时,我总被一个问题困住:古代人怎么就那么排斥新技术?不管是皇帝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面对从没见过的器物、思想或发明,第一反应几乎都是抵触。我当时满心疑惑:技术明明能让生活变方便,能创造财富,这不是明摆着的好事吗?我一个 16 岁的学生都能想明白,难道古人都看不懂?

直到上了大学,读了越来越多的史料和研究,我才慢慢琢磨透:古人害怕的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背后必然带来的 “变化”。稳定,才是他们心中压倒一切的核心诉求,哪怕牺牲效率也在所不惜。
先讲个罗马帝国的真实故事。公元 1 世纪,罗马出了个特别会经营国家的皇帝 —— 韦斯巴芗。他在位时重建了帝国秩序,把空虚的国库打理得满满当当,是出了名的务实君主。有一天,一位工匠兴冲冲地献上了一台新发明的机器,这台机器能大幅节省人力,不管是灌溉农田还是搬运货物都能用。韦斯巴芗看了演示,当场下令重赏工匠,可赏完之后却脸色一沉,命令工匠:“这东西再也不许造了,也不许让别人知道怎么造。”
很多人觉得韦斯巴芗愚昧,放着能提高效率的技术不用。但其实他一点不傻,他比谁都清楚技术能带来财富,可在古代社会,财富从来不是最稀缺的东西,稳定才是。技术确实能提升生产率,但它绝不会只停留在 “提高效率” 这一步 —— 它会悄悄改变财富分配,打乱原有的生产关系,甚至撼动阶层力量对比。而这些变化,根本没人能预料到后果,这才是最让统治者忌惮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17 世纪时,一位法国传教士历经千辛万苦,穿越原始森林见到了老挝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苏里亚翁萨。传教士看着王国里泥泞难行的道路,向国王建议:“陛下,要是能修建公路和运河,您的王国一定会变得空前富饶,我下次来也不用这么艰辛了。” 苏里亚翁萨却笑着摇了摇头,平静地回答:“如果修了平坦的公路和畅通的运河,外敌和叛军不也能畅行无阻吗?现在这样,虽然不富裕,但很安全,挺好的。”
19 世纪初,大哥伦比亚总统玻利瓦尔 —— 就是那位带领南美各国摆脱殖民统治的 “解放者”,写信给巴拉圭执政官弗朗西娅博士,劝他打开国门,引进新技术和外来贸易,让国家发展起来。可这位狡黠的独裁者回信说:“感谢你的好意,但我们宁愿在泥巴里过活,也不想冒那些未知的风险。”
到了 20 世纪中期,扎伊尔的暴君蒙博托看到邻国布隆迪的总统被人民起义赶下了台,特意写信 “嘲讽”:“我早告诉你不要修路,现在好了吧?他们就是开着车,沿着你修的路来反对你的。” 他还得意洋洋地补充:“我统治扎伊尔 20 年,一条公路都没修过,所以我的王位稳如泰山。”
从英明的明君到残酷的暴君,他们的共同点的是:都知道技术能带来财富,但更清楚技术意味着变化,而变化就等于风险。在他们眼里,与其冒着失去权力的风险追求不确定的财富,不如守住眼前的稳定更靠谱。
不光是世俗统治者,宗教权威也一样。15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教廷曾经热烈拥抱过一项新技术 —— 印刷机。宗教传播本来就需要大量的文本,拉丁文圣经、宗座御令、号召十字军东征的传单,这些东西印得越多越好,印刷机的出现刚好满足了教会的需求,让他们能快速、大量地传播教义。
当时天主教会还在为西斯廷礼拜堂的建筑经费发愁,正在大举兜售 “赎罪券”—— 信徒只要花钱购买,就能被赦免罪孽,死后还能上天堂。赎罪券卖得异常火爆,教会为了赚更多钱,干脆把赎罪券也加入了印刷清单,一时间,欧洲各地都能看到印刷的赎罪券传单。
可教会万万没想到,印刷机这东西是 “双刃剑”,一旦启动就再也不受控制了。没过几年,从印刷机里滚出来的,可不只有赎罪券和圣经,还有各种政治传单、用俗语翻译的圣经译本,以及马丁・路德的《95 条论纲》。路德的论纲直指教会兜售赎罪券的腐败行为,通过印刷机快速传遍欧洲,点燃了宗教改革的导火索。
这时候教会才恍然大悟,自己被技术 “坑” 了。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对所有人都有利,但如果既得利益者的损失比对手大,那技术对他们来说就是有害的。为了挽回局面,教会发明了一项新制度 —— 出版审查,这个制度的生命力远比印刷机顽强,直到今天还在某些地方存在。可木已成舟,印刷机带来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已经再也无法挽回了。
远在东方的奥斯曼帝国,亲眼见证了基督教世界因为印刷机而分裂的全过程,他们吸取了教训,成功把这股 “风险” 掐灭在了萌芽状态。1492 年,被西班牙驱逐的犹太人把印刷机带到了土耳其,可伊斯兰教士阶层立刻发布禁令:禁止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或土耳其文印刷书籍。在之后的 200 多年里,整个奥斯曼帝国都没有一本本土语言的印刷书。
有人说土耳其的统治者太愚蠢,错过了技术发展的机会。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太聪明了 —— 通过禁止印刷术,他们维护了伊斯兰教逊尼派的统一,避免了思想混乱和教派分裂,眼睁睁看着基督教世界陷入长期的内斗。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无疑是维护帝国稳定的 “明智之举”。

其实不光是统治者,古代的老百姓也一样害怕新技术。19 世纪初的英国,就发生了著名的 “卢德运动”。当时工业革命刚刚兴起,纺织厂开始使用蒸汽机和自动化纺织机,这些机器效率极高,一台机器能抵得上十几个工人的工作量。结果就是大量手工业工人失业,而那些保住工作的工人,也不得不面对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恶劣的工作条件,工资却没涨多少。
愤怒的工人们找不到出路,只能把怨气撒在机器上,他们成群结队地冲进工厂,捣毁纺织机,认为是这些 “怪物” 抢走了他们的生计。在今天看来,卢德运动是 “反进步” 的,但站在当时工人的角度,他们的恐惧是真实的 —— 新技术没有让他们的生活变好,反而让他们陷入了绝境。
中国近代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1876 年,英国怡和洋行在上海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营业性铁路 —— 吴淞铁路。这条铁路全长 14.5 公里,火车时速能达到 32 公里,比当时最快的马车还快好几倍。可铁路建成后,却引发了轩然大波。京师百姓从没见过这种 “铁疙瘩” 在铁轨上飞驰,纷纷传言这是 “妖物”,会破坏风水、惊扰祖先。有人说火车开动时的轰鸣声会震得地动山摇,有人说铁轨会阻断地下的龙脉,甚至还有人声称看到火车撞死人(其实是有人故意破坏铁路导致的事故)。

最后,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花了 28.5 万两白银买下了吴淞铁路,然后下令把铁路拆毁,铁轨和火车都扔进了大海。当时的老百姓和官员,并不是不知道火车比马车快,而是他们害怕这种新技术带来的变化 —— 铁路会打破原有的交通格局,让依靠水路和陆路运输为生的船夫、车夫失业,还会冲击传统的社会秩序和观念。
义和团运动时期,拳民们不仅攻打外国使馆,还疯狂破坏铁路、电报线、工厂机器。他们喊着 “扶清灭洋” 的口号,认为这些 “洋玩意儿” 是导致国家衰败、百姓受苦的根源。其实义和团的大师兄们和八旗勋贵一样,都对新技术充满恐惧,只是他们表达恐惧的方式更极端 —— 通过破坏来抵制变化。
还有印度的例子。直到今天,印度农村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在家里建厕所,很多人觉得这是 “愚昧”“不讲卫生”。但背后的原因远比这复杂:在印度传统社会,厕所被认为是 “不洁” 的,而室内厕所是英国殖民者带来的 “外来事物”。印度老百姓痛恨的不是厕所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殖民统治和文化入侵。他们害怕接受这些 “新事物”,会让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消失。
喀麦隆的老百姓曾经拒绝接种疫苗,也不是因为迷信。他们记得,当年法国殖民者就是以 “打疫苗” 为借口,强行抓走他们的孩子,把他们送到种植园做苦工,或者征召入伍。所以当现代疫苗再次进入喀麦隆时,老百姓的第一反应是恐惧和抗拒 —— 他们害怕历史重演,害怕新技术背后隐藏着新的剥削。
为什么古代社会上上下下都如此害怕技术带来的变化?这就要从古代社会的本质说起。经济史学家把古代世界称为 “马尔萨斯世界”,这个世界受马尔萨斯 - 李嘉图定律支配,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可持续的指数增长,到处都是残酷的存量竞争和零和博弈。
简单来说,古代社会的财富总量是固定的,有人多拿一点,就必然有人少拿一点。技术创新偶尔会带来一些 “增量”,但这些增量很快就会被人口增长消化掉。比如某个地方发明了新的耕作技术,粮食产量增加了,可过不了几年,人口就会因为粮食充足而增长,最后每个人的平均粮食占有量还是和以前一样,生活水平始终在温饱线上徘徊。
古代最富有的国家,是 18 世纪末的荷兰共和国,它的国民收入也只是温饱线的 3.5 倍。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想要比荷兰富有,根本不用提高人均收入,只要人口达到荷兰的 4 倍就行。这种情况下,技术创新带来的那点增量,根本改变不了什么,反而可能打破原有的利益平衡。
而且在古代,世界的基本面貌几千年来都没怎么变过。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古埃及,和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时期的埃及,军队在巴勒斯坦的行军速度差不多 —— 因为路还是那么破,交通工具还是马车和骆驼。汉武帝时期的中国和华盛顿时期的美国,城镇化率也差不多,最多只有 20%,绝大多数人还是农民。哈伦・拉希德时代的阿拉伯帝国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区别,都用着简陋的农具,靠天吃饭。查士丁尼一世统治下的东罗马帝国和苏莱曼一世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东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数量相差无几,人们的平均寿命也都是 35 岁左右。

如果一个唐朝人穿越到明朝,他根本不用花太多时间适应 —— 衣服样式可能有点变化,但耕作方式、生活习惯、社会结构都和他熟悉的时代差不多。在这样的环境下,古人自然会认为世界是停滞不前或者循环往复的,他们无法想象技术能彻底改变这个世界。
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有这样的认知:中国人看到的是王朝兴衰的周期律,一个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然后被另一个王朝取代,周而复始;古埃及人相信神话会不断重演,法老的统治会像尼罗河的泛滥一样,定期更迭但本质不变;日本人相信 “皇国永续”,认为他们的社会秩序永远不会改变;古伊朗人相信世界上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善恶的较量会一直持续;佛教徒和古希腊人则认为,时代是不断退步的,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更糟糕;基督徒和穆斯林常常宣扬 “末日近了”,认为世界不会有本质的进步,只会走向终结。
在这样的认知下,谁要是相信技术能彻底改变这个几千年来都没怎么变的世界,反而会被当成疯子。所以当新技术出现时,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会本能地警惕 —— 统治者担心失去权力,被统治者担心日子过得更糟。在零和博弈的世界里,没人相信 “双赢” 的存在,大家都觉得别人的 gain 就是自己的 loss。
而现代社会则完全不同。工业革命之后,效率突然变得比稳定更重要了,世界进入了指数增长的时代。现代社会的人均收入能达到温饱线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我们习惯了每年都有新发明问世,习惯了经济不断增长,甚至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新技术、没有增长会是什么样子。

但这里有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宇宙中真的存在永不停止的指数增长吗?工业革命以来这二百年的日新月异,会不会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短暂片段?终有一天,技术发展会不会抵达极限,人类又会回到 “稳定高于效率” 的状态?或者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技术进步会打破阶级壁垒,让人类迎来空前的解放,从此迈向更广阔的宇宙?
这些问题太过宏大,远远超出了一篇文章能讨论的范围。但至少和古人相比,我们有了想象的自由 —— 我们可以想象技术带来的无限可能,也可以思考未来的各种走向。这种天马行空的思考,是困在马尔萨斯陷阱里的古人无法理解的。
技术的魔力,从来都不是天生的。它只是到了工业社会,才因为能带来持续的增长和进步,而变得如此迷人。古人不是愚昧,他们只是生活在一个 “稳定至上” 的时代,他们的观念和选择,都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必然结果。
想要理解古人的行为,就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评判,而要回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感受那份对稳定的渴求,和对变化的恐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古人对技术的恐惧,本质上是对未知变化的恐惧,是对稳定生活的守护。
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坦然拥抱技术,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不是因为我们比古人更聪明,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 “变化至上” 的时代,技术带来的不再是零和博弈的风险,而是共赢的可能。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古人的恐惧并非毫无道理 —— 技术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带来进步,也能带来混乱。如何在拥抱变化的同时,守住稳定的底线,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思考的新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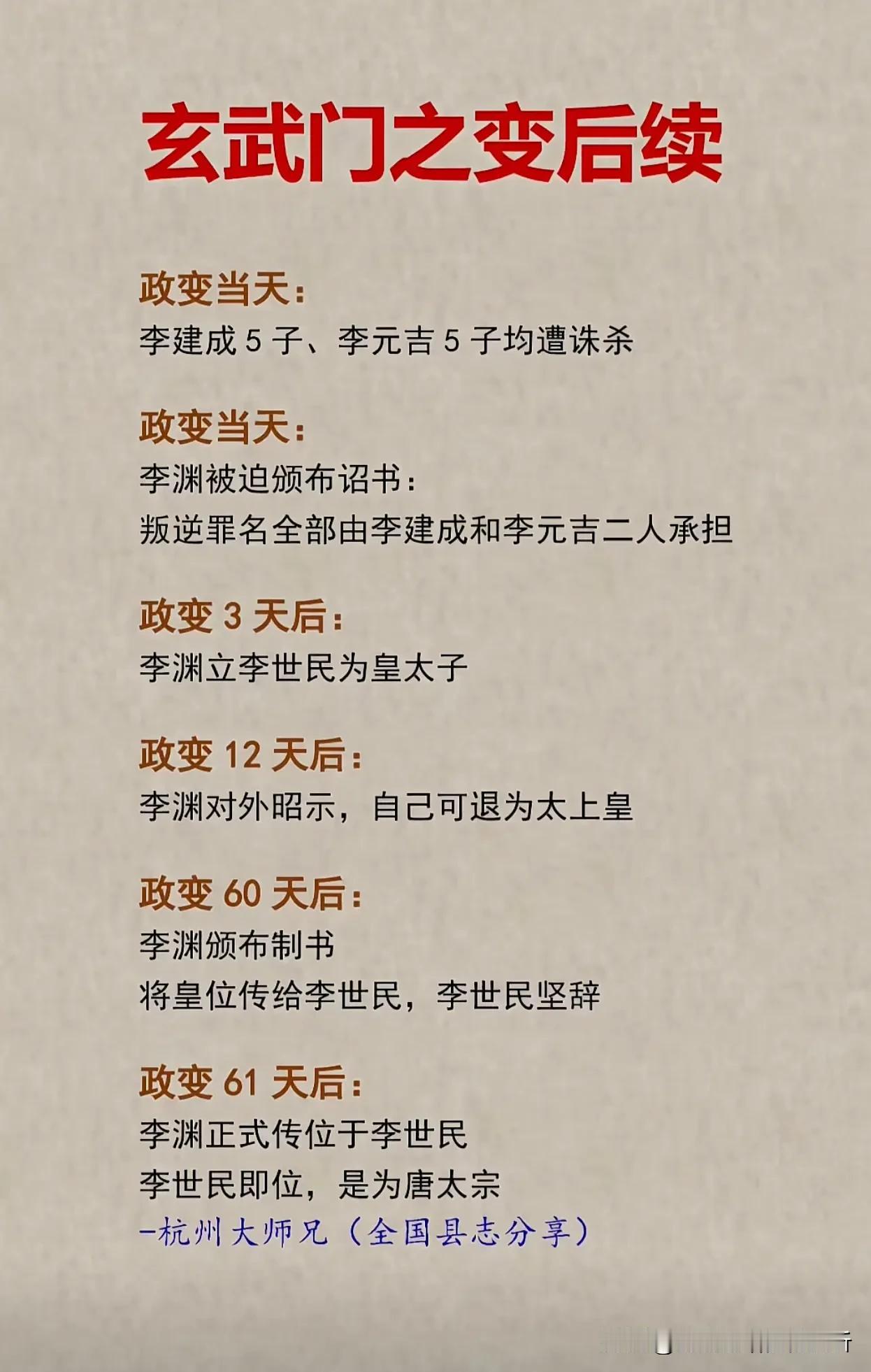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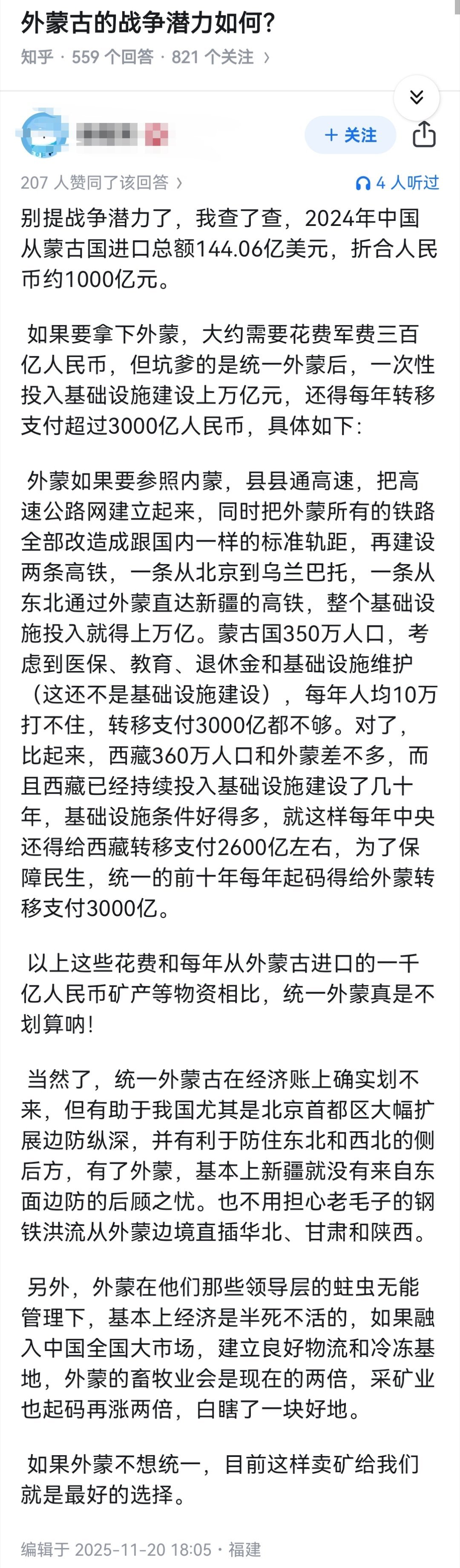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