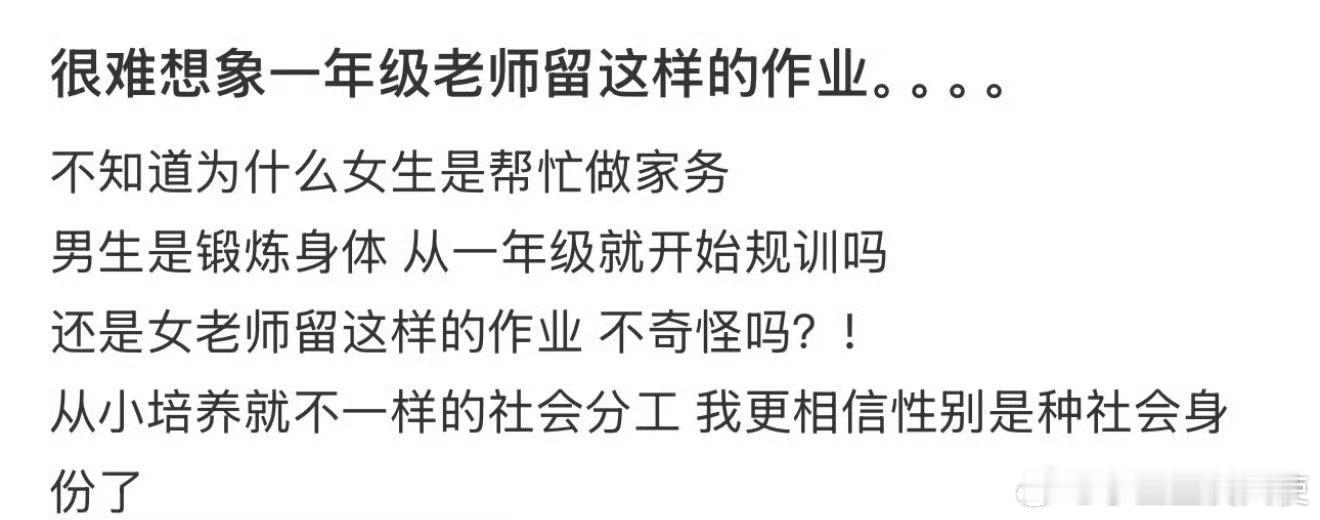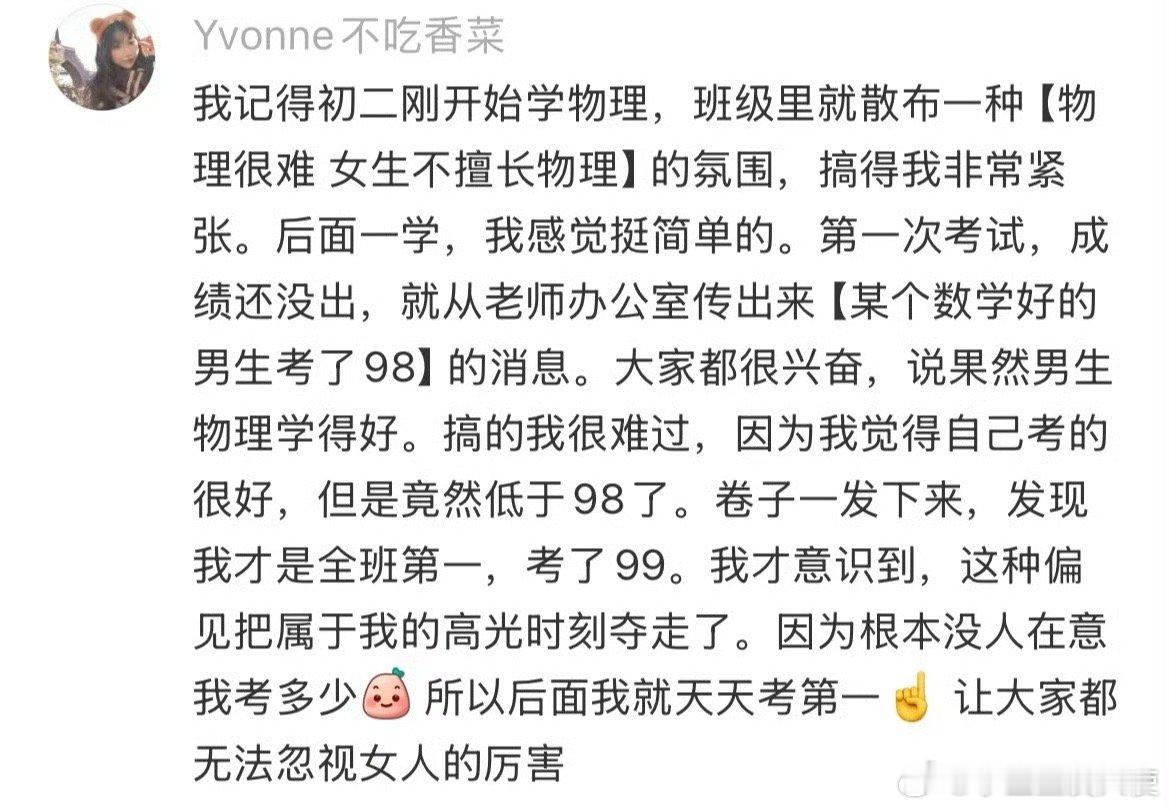“国家的一大损失!”2000年,山东有一神童,短短的2天便念完小学,10岁那年参加高考,考出了566的高分,但他却只读了1年大学,就嫌弃太简单回家了,如此的奇人令人好奇之余,又感到十分质疑,究竟是觉得大学太简单,还是被打回原形了! 把画面放回2010年山东的高考考场,教室里坐着一排排18岁上下的考生,空气里是那种混着墨水味、汗味和紧张感的闷。 就在这群人中间,有一个孩子怎么看都不“对劲”:个头很小,坐到椅子上腿还够不着地,脚尖在下面晃来晃去,拿笔的动作却很稳,神情也不像周围人那样绷着。 他叫苏刘溢,那一年只有10岁,等成绩出来,数字一下把很多人震住:总分566分,数学130,理综181。 对普通家庭和普通考生来说,这是需要连续多年高强度训练,才能摸到的分数线;更别说出现在一个10岁孩子身上,冲击力自然更大,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他厉害”,而是“这怎么可能”。 当时也出现了一个现实问题:天赋再显眼,制度还是制度,山东大学方面对他的能力评价很高,但录取程序、年龄、学籍等一系列硬性条件摆在那里,学校并不容易为一个特殊个案开门。 反倒是当时,正在推进新型办学模式的南方科技大学,拥有更大的试验空间,2011年3月,南科大把他招进首届实验班,他成了那批学生里年纪最小的一个。 为了让他能在校园里生活下去,学校给出的支持力度很大:学费免除,生活补助,甚至允许母亲在校陪读,并安排母子住在一起。 这些安排不难理解,一个11岁左右的孩子,放进大学环境,不提供额外照顾几乎无法运转。 那段时间媒体也很热衷报道,“神童”“中国版谢尔顿”之类的标签迅速贴上来,他成了典型的“被讲述对象”。 但四个月后,事情急转直下,2011年7月,他离开学校回家,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课程太简单”。 舆论场很快翻脸:上一秒还是“天才样本”,下一秒就有人开始说“伤仲永”,把他的退学当成一种“陨落”。 如果只看结果,确实像突然熄火;但把时间往更早的节点推,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埋下了。 2007年前后,他7岁进入当地小学,短时间内就出现严重不适应,一个智力发展明显超前、表达方式又和同龄人不同的孩子,在低龄集体里很容易被当成“怪人”。 同学不理解、排斥甚至欺负,并不需要复杂理由,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他不一样”,孩子如果还小、身体也弱,面对这种局面,往往没有自保能力。 对家长来说,跳级有时不是“拔苗助长”,更像一种逃离:把孩子从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环境里拉出来,送到更大年龄的群体中去。 因为在更大的孩子眼里,“会学、学得快”至少可能转化成一种尊重,而不是纯粹的异类。 于是苏刘溢一路往前赶,跳级成了他成长轨迹的一部分,外界看到的是速度:很小就学完了别人需要很多年完成的内容;家里人面对的则是更现实的选择:如果不让他一直“往上走”,他在同龄环境里可能会一直受伤。 可到了大学,规则突然变了,大学并不只是更难的课题、更高阶的知识,它还是一个复杂的人际与生活系统:宿舍关系、社团活动、团队项目、师生边界、同学之间的交往尺度,这些都要求一个人具备与年龄相匹配的自控、沟通、责任意识。 苏刘溢在智力层面可能很突出,但心智、生活技能和社交经验,却很难靠跳级“同步升级”。 这种错位,会在很多小事上暴露出来:课堂上坐不住、觉得无聊就乱动;对别人身体界限没概念,去拽同学头发这种行为,在小学都可能惹麻烦,更别说大学。 实验室对安全规则要求极高,孩子如果还停留在“好奇就去试试”的阶段,就很容易做出危险举动;生活上也需要依赖陪读的母亲,洗衣、吃饭、作息都还像小学生。 甚至连宿舍夜聊,这种普通大学生活,对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都是不可能同步的:别人聊恋爱、社团、人际,他九点就困到必须睡觉,这不是“高冷”,是生理节律和心理阶段还没到那一步。 更关键的是学习方式,一个早熟的孩子,很容易形成“靠自学单打独斗”的知识体系,但大学课程往往要求协作:分工、讨论、汇报、组队做项目、面对冲突和妥协。 对一个年纪太小的人来说,真正难的未必是知识本身,而是这种“成人世界的组织方式”,在这种压力下,“课程太简单”,也可能是一种更容易说出口的理由——至少能维护自尊,避免承认“我其实是适应不了”。 后来他彻底淡出公众视野,这一点对他个人未必是坏事,一个孩子被反复围观、被贴标签、被当成“样本”,很容易把人生过成别人的实验。 从这个角度看,他当年离开南科大未必是“断崖式下坠”,更像一次及时刹车,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被推到大学、被推到舆论中心,本来就极容易出问题。 退下来、慢一点、回到更符合年龄的成长节奏,反而可能是对他最现实的保护。 信息来源:《神童小学只读了3天,10岁便上了大学,因一事被学校劝退》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