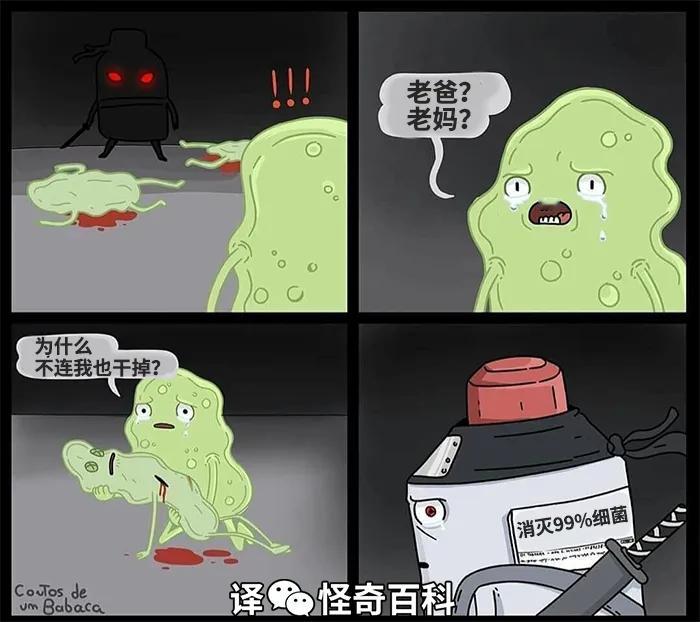记录者 欧美人种的MV杂合子比例高达40-50%,有些人可能理解不到这个数字背后的含义。这并不是说白人的祖上有一半都食过人,所以这个数字占比接近一半,而是说明他们曾经经历过大量、长期、全面的食人时代,淘汰掉了几乎所有的朊病毒抗性低的MM、VV纯合子,只剩下了抗性极高的MV杂合子。
这是一段令人脊背发凉的基因历史。MV杂合子是朊病毒致病机制下的“幸存者密码”,但这种遗传密码并非无由而来。它是淘汰的产物,是依赖某种激烈的人类行为——食人——的血腥筛选。在没有抗性的个体被逐一“移出游戏”后,欧美人种中留下来的,便是具有一定抗性的杂合子,演绎出这一惊人的比例。
MV杂合子因为遗传性的特点,其后代中会出现MM、MV、VV三种类型,比例大致为1:2:1。因此,在一个没有继续繁衍大规模朊病毒感染的环境中,MV杂合子的比例可以稳定在50%,这是进化意义上的上限。这样的遗传稳定性背后却隐藏了一段不容忽视的历史影像。问题是,这份历史并不是蒙尘的档案或遥远的传说,而是被写进了基因的钟摆里,成为记忆架构的一部分。
古代欧洲的“食人”并非只是恐慌与饥饿引发的偶然灾难,它竟然有了一整套“理论基础”。《约翰福音》中耶稣的教诲——“食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是否过于直白?尽管学者们在解释这段话时会倾向于走向转喻的精神意义,但在一个既迷信又野蛮、且资源骤然稀缺的环境下,宗教教义有时可能就变成了行为合法性的遮羞布。特别是在中世纪横扫欧洲的恐怖大瘟疫——黑死病来袭时,社会结构陷入了瓦解,生存的本能让一些人大概真的选择了不择手段地活着。
是否“食人”这种极端行为真的曾为防止绝望而现身于欧洲大规模的历史场景中?试想,黑死病的三百年噩梦,几乎削减了当时欧洲一半的人口。尸体堆积如山,火化能力与掩埋资源远远不足。这是一场生命被屠戮的循环:瘟疫带来死亡,死亡带来生存竞争,而生存竞争又推动了极端选择行为的产生。对于饥饿与希望无限压缩的普通人而言,“食物”逐渐突破禁忌的界限,成为“以肉续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欧亚人的基因密码中,乃至历史记载中,“吃人”并非完全藏匿。即便到了文明开化的后期,这在白人殖民史中仍有蛛丝马迹可寻。“把木乃伊磨成粉,再卖到药房里。”这听上去像是愚昧的笑话,但事实上,19世纪的欧洲,医药市场上流行着木乃伊制成的粉末,号称“能治百病”。食人文化从未真正远离,或许只是以“改头换面”的方式潜伏在吃药的仪式里,在宗教隐喻的包裹下,擦去原本的耻辱。
从基因到宗教,从鼠疫到亡者利用,这一切似乎叠加着某种逻辑——当生存底线被击穿,伦理可能被利益拉低至一种动物性的裸态。无独有偶,疫情与瘟疫,总是推动人群朝某种方向加速进化。所谓大瘟疫影响基因库的说法,不无道理。而这基因库成型的过程,本身就包含了许多不堪回首的“筛选条件”。
相比之下,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中的鼠疫对于人种基因影响较小?或许部分原因在于,社会组织结构、粮食储备、交通条件等一直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古代的鼠疫,尽管频繁,但多集中于小范围区域甚至单个村落,很少具备全社会性的毁灭力。而中世纪的欧洲,人口密度高但交通管控涣散,教会力量对实际公共卫生的组织能力却乏善可陈。鼠疫俨然成为了整个封建体系不可逆转的崩塌点,也可能成为朊病毒在群体中横行肆虐的绝佳契机。
至此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如果基因的历史是被“纪录在身体的殿堂中”,那么这场由食人增幅的进化,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唯状态论”生存法则的诠释。今天的我们难以彻底揭开历史的创口,这剧情悖论式的残酷也无法复制,毕竟现代社会的进化选择已经不再围绕着生理问题展开。
食人历史看似冷血无情,但它又歪打正着地成为了免疫进化的“试金石”。34亿细胞的沉默大合唱中,或许流淌着亘古的暗语:挣扎的种族,终究进化为今天的文明种群。只是这代价,太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