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叔当年干民兵营长时,保护一个下放的老干部,后来这个老干部落实政策回城了,当了副部级干部,我二叔就去找他,请他帮子女安排工作,这位干部根本不理我二叔。 那天晚上村支书走后,二叔真就翻来覆去一宿没睡。天快亮时,他窸窸窣窣地摸下床,从柜子最里头翻出个手绢包,里头躺着那支旧钢笔。窗外的天色是鸭蛋青,他看着笔帽上斑驳的漆,点了一支烟。 二婶也醒了,靠在门框上小声问:“真要去?”二叔没吭声,只是把烟抽得滋滋响。堂哥堂姐那屋传来轻轻的咳嗽声,两个孩子其实也醒着。二叔忽然就把烟掐了,把手绢重新包好,塞回了柜子深处。“不去了。”他说,声音有点哑。 二婶愣了愣。二叔走到院子里,舀了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喝下去,抹了把嘴:“老陈有老陈的难处。咱孩子有手有脚,干嘛非去求那扇敲不开的门?”堂哥堂姐这时也出来了,眼睛都亮晶晶地看着他。堂姐说:“爸,我跟同学打听过了,县里新开的纺织厂在招工,俺想去试试。”堂哥也跟着点头:“我力气大,去建筑队也行。” 事情就这么定了。二叔把那三百块钱分成两份,给两个孩子当路费和头个月的生活费。送他们去县城坐车那天,风有点大,吹得人衣服鼓鼓的。二叔就站在土路边上挥挥手,什么也没嘱咐。 堂姐心细,在纺织厂从挡车工干起,下班就抱着专业书啃,后来竟考进了厂里的技术科。堂哥在建筑队晒得黝黑,专挑最苦的活儿干,慢慢带起了自己的小班组。都没大富大贵,但日子眼见着踏实起来。 去年老陈去世的消息登了报,很小的一个讣告。二叔戴着老花镜,就着窗外的光看了好久。吃饭时他忽然说:“那支钢笔,笔尖其实早就写秃了。”大家都没接话。院子里,他去年栽的葡萄藤正顺着架子往上爬,绿莹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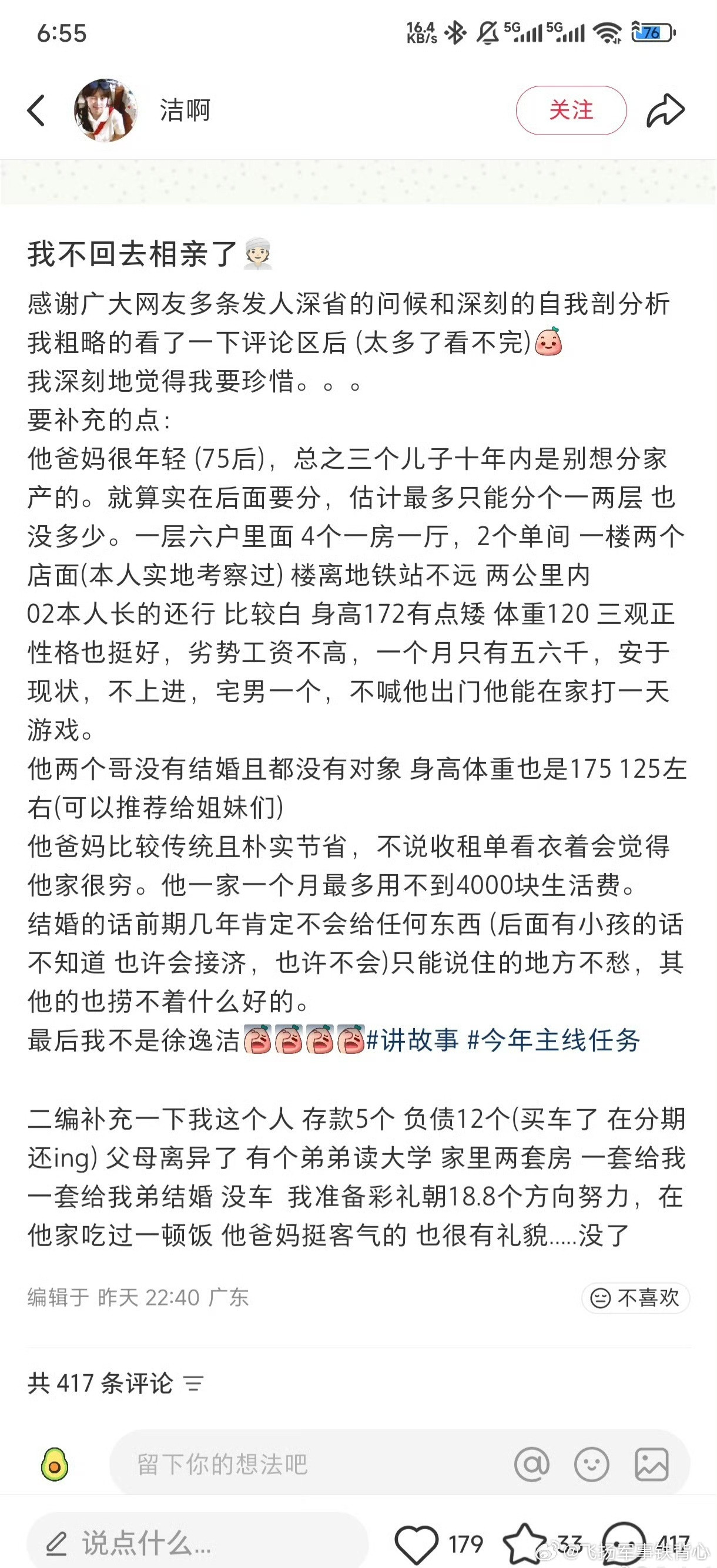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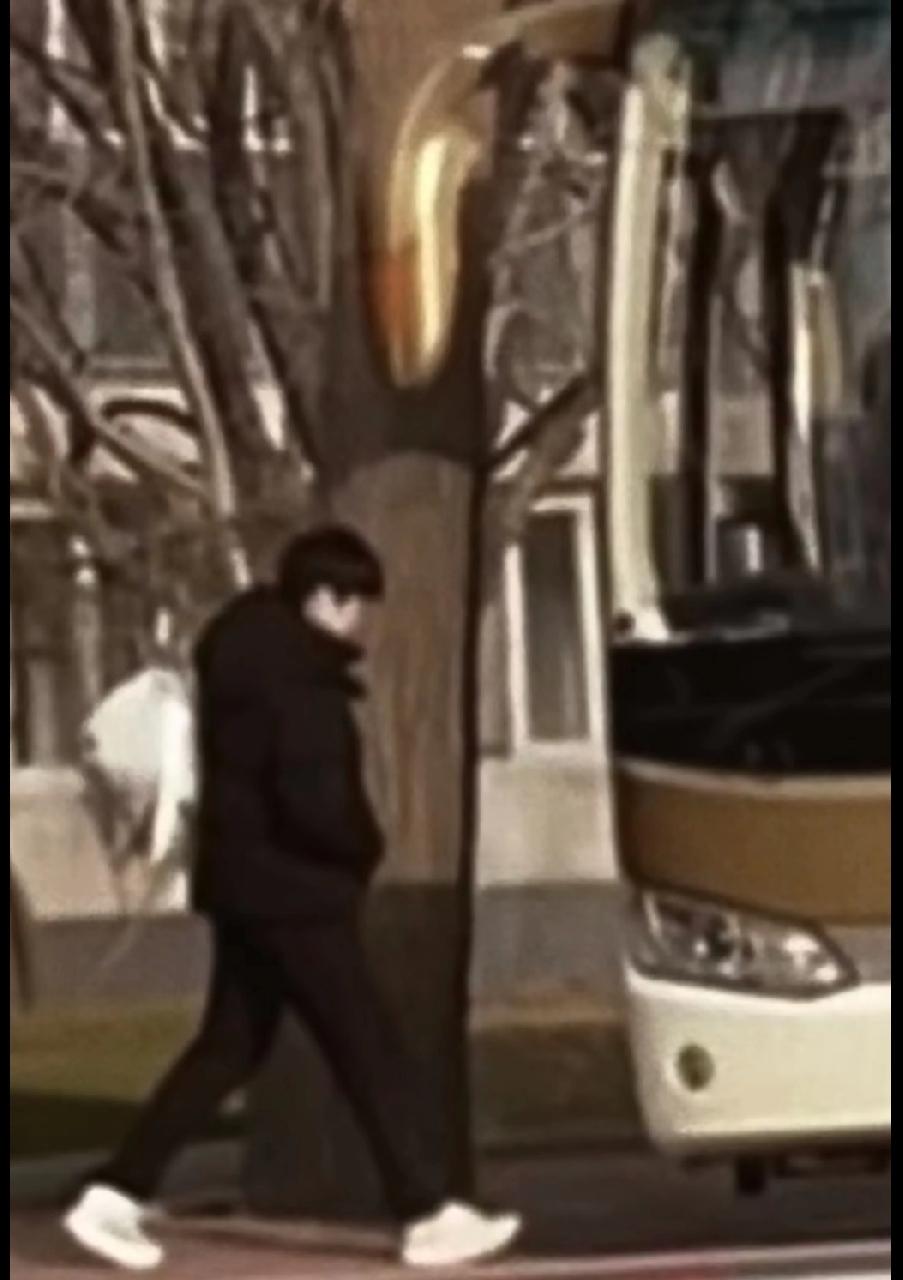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