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52岁的金庸爱上16岁女招待。他想要和妻子离婚,妻子说:“可以,但是那个女的必须绝育”。金庸才答应没多久,他的长子就美国自缢身亡了。 1976年的那个秋天,对于武侠宗师金庸而言,或许比任何一部小说都要寒意刺骨,所有的体面与传奇,最终都被一张藏在衣兜里的珠宝店收据撕开了缺口,在此之前,他早已是香江文坛的执牛耳者,是一呼百应的查良镛。 但在那一刻,在那张年轻女孩佩戴的项链发票面前,他只是一个被结发妻子从口袋里翻出“罪证”的中年男人,这段婚姻的坍塌,并没有那些小说里轰轰烈烈的复仇情节,反而冷静得让人心悸。 此时的朱玫,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港大高才生,生活把她磨砺得更像是一个刚硬的合伙人,回望二十年前,她也曾是拿着笔杆跑新闻的记者,可为了那个共同的“武侠梦”她把自己活成了这世上最能吃苦的女人。 那是怎样的日子,是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校对稿件,是凌晨顶着星光去码头等廉价的渡轮,甚至是把作为女人最珍视的首饰拿去典当,换回满屋刺鼻的油墨味,为了创办《明报》,她把自己揉碎了,填进丈夫事业的地基里。 可人到中年的金庸,已经不需要一个会对他鞋子乱放而唠叨的“合伙人”他更沉溺于弥敦道某家酒廊里那个年轻女孩的仰望,那个叫林乐怡的服务生,年轻、柔软,不懂报社的生存压力,只会说一句“查先生,你皱眉的样子真好看”。 一边是家中日渐急躁、嫌他稿纸太乱的妻,一边是把他奉若神明的如花美眷,这张价值不菲的项链收据,成了两个女人命运的分水岭,金庸把仅剩的温柔给了那个会崇拜他的女孩,却把那个为了五斗米陪他熬干心血的女人推向了深渊。 当朱玫拿着收据,直接找到两人约会的场所时,她没有歇斯底里地撒泼,她甚至在看清那个比自己年轻太多的女孩时,展现出了一种近乎残酷的冷静,她没有挽留这个想要离婚的男人,只是在沉默许久后,开出了放手的筹码。 她要求那位渴望嫁入才子家门的年轻姑娘,必须接受输卵管结扎手术,这个决定听起来狠辣绝情,却是一个母亲在绝境中最后的防守,她不能让任何不确定的因素,威胁到自己膝下四个孩子的权益与未来,她太懂这个男人了,既要成全他的新欢,就要锁死他再育的可能。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金庸点头了,在那场足以改变三个家庭命运的谈判里,五十二岁的他,为了尽快从这尴尬的围城中解脱,答应了这近乎苛刻的交换条件,随着婚书作废,这个原本看着光鲜的豪门之家,像是被抽去了脊梁,开始从内部迅速瓦解。 报应来得猝不及防,最先崩塌的是被朱玫寄予厚望的长子查传侠,这个被外界誉为“小查良镛”的天才少年,三岁背诗,十一岁发表文章,本该是延续金庸才情的最完美作品,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父母离异的消息像一把重锤,砸在了原本就深陷学业与情感困境的少年心上。 那个令人窒息的深夜,十九岁的儿子拨通了越洋电话,而电话那头的父亲,或许正忙着构思韦小宝的某个风流段落,或许正忙着处理报馆的琐事,匆匆敷衍几句便挂断了,如果那一刻金庸能停下笔,哪怕只是多问一句,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这一记耳光,打得金庸灵魂出窍,他在虚构的江湖里写尽了千重情义,能让笔下的大侠起死回生,却救不回自己儿子的命,那个曾经为了孩子甚至愿意去摆地摊的朱玫,听到死讯时彻底碎了。 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最引以为傲的长子,她甚至拒绝了前夫一切形式的经济援助,在后来漫长的余生里,这个倔强的女人宁愿顶着满手冻疮在街边卖杂货、深夜在灯下替人抄书,也不愿再向那个“功成名就”的男人低头。 金庸再婚了,娶了那个做完手术、永远带着一丝愧疚的林乐怡,而朱玫,在孤独中一点点熬干了自己的生命,1998年,当她在医院的病床上独自离世时,身边没有亲人,没有鲜花,只有那张记录死亡的通知单。 据传,在她弥留之际的床头,放着一本翻得卷边的《明报创刊十周年特刊》那里面夹着一张照片,是一对年轻夫妇在寒风中微笑着互相打气的模样,那时候他们一无所有,却拥有彼此最完整的灵魂。 许多年后,满头白发的金庸对着镜头流泪,哽咽着说此生最对不起的人是朱玫,可这迟来的深情,终究太轻了,正如那句老话所言,共苦易,同甘难,他在书中给了韦小宝圆满的结局,却把这一地无法收拾的玻璃渣,留给了现实中那个陪他打天下的发妻。 信息来源:-10/02/10-71E7CC2C1CB0CFA748256DB30009DE8F.htm光明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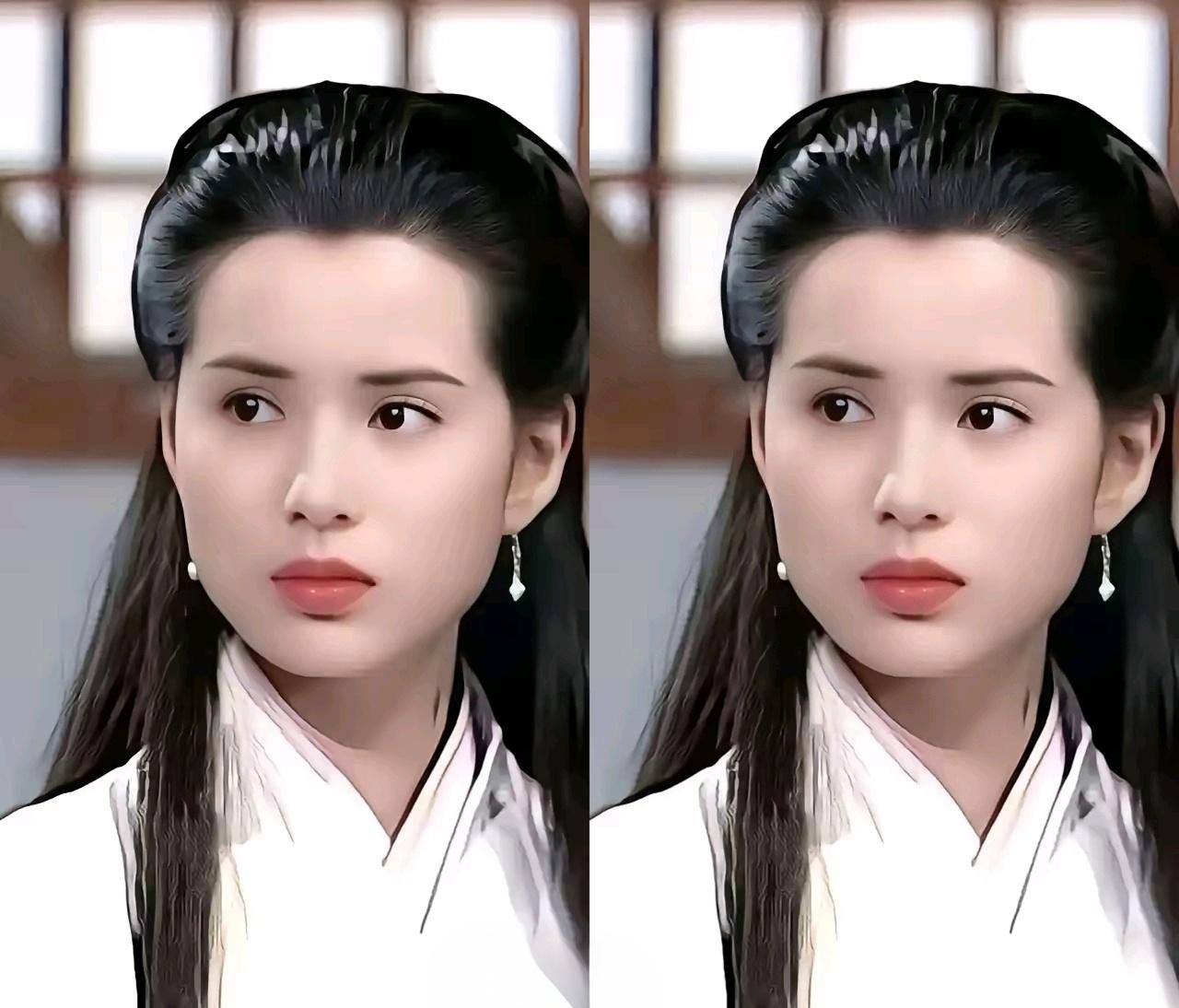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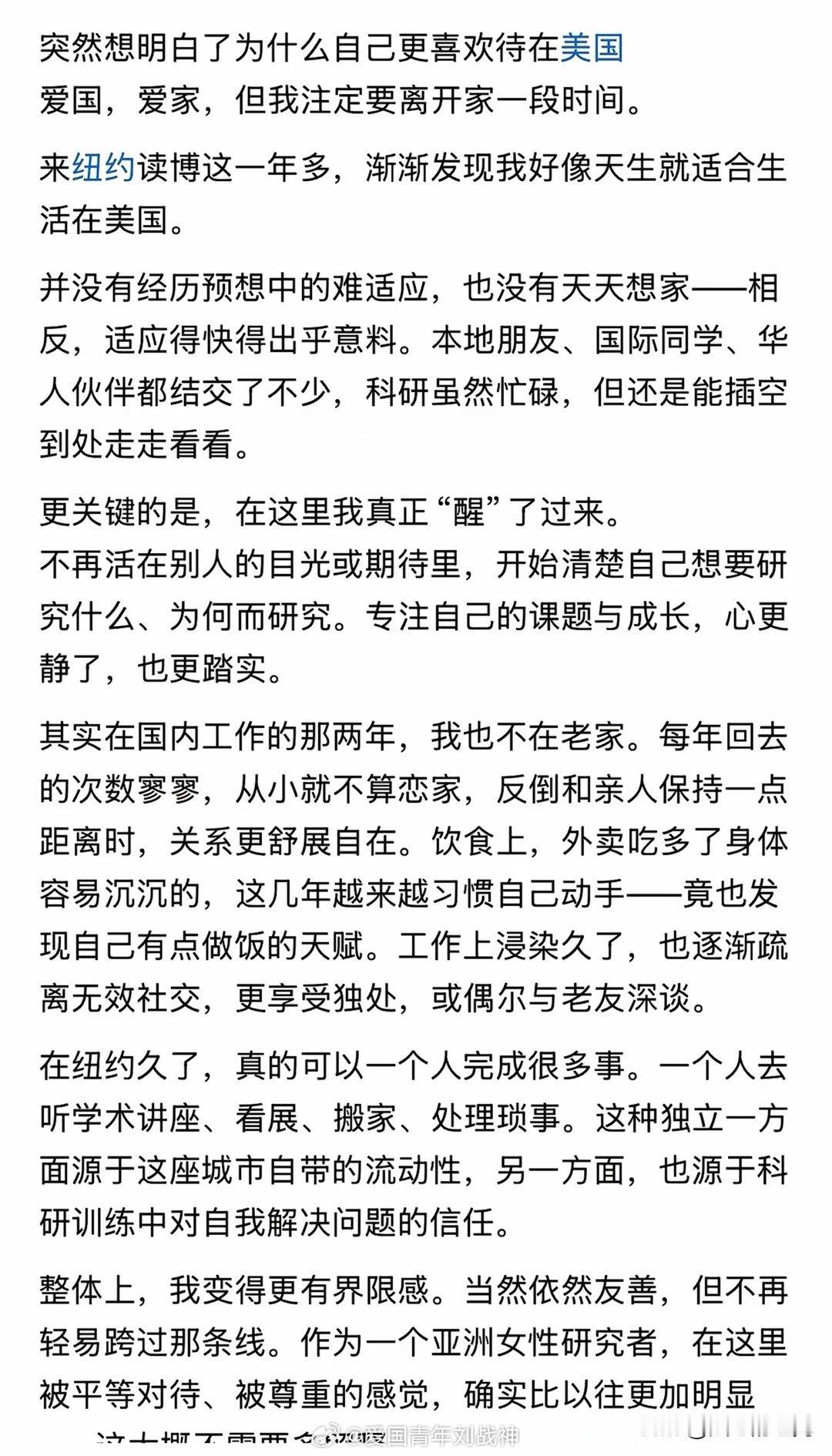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