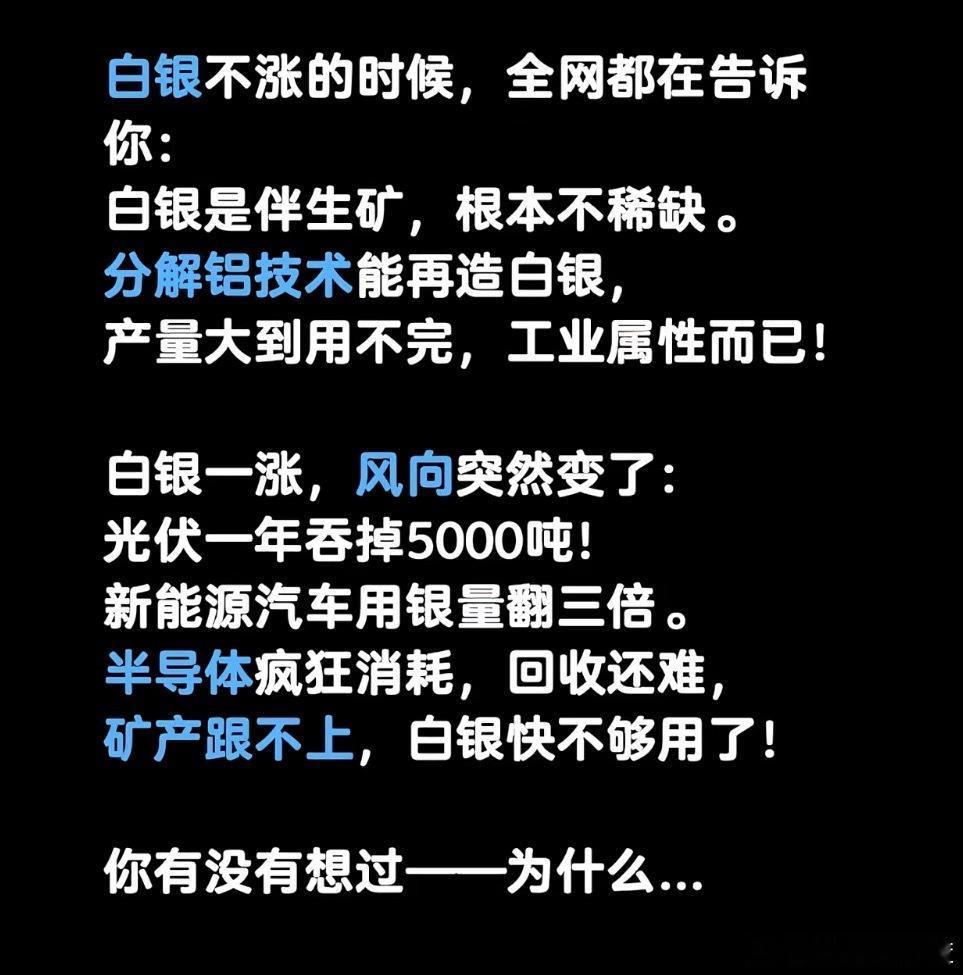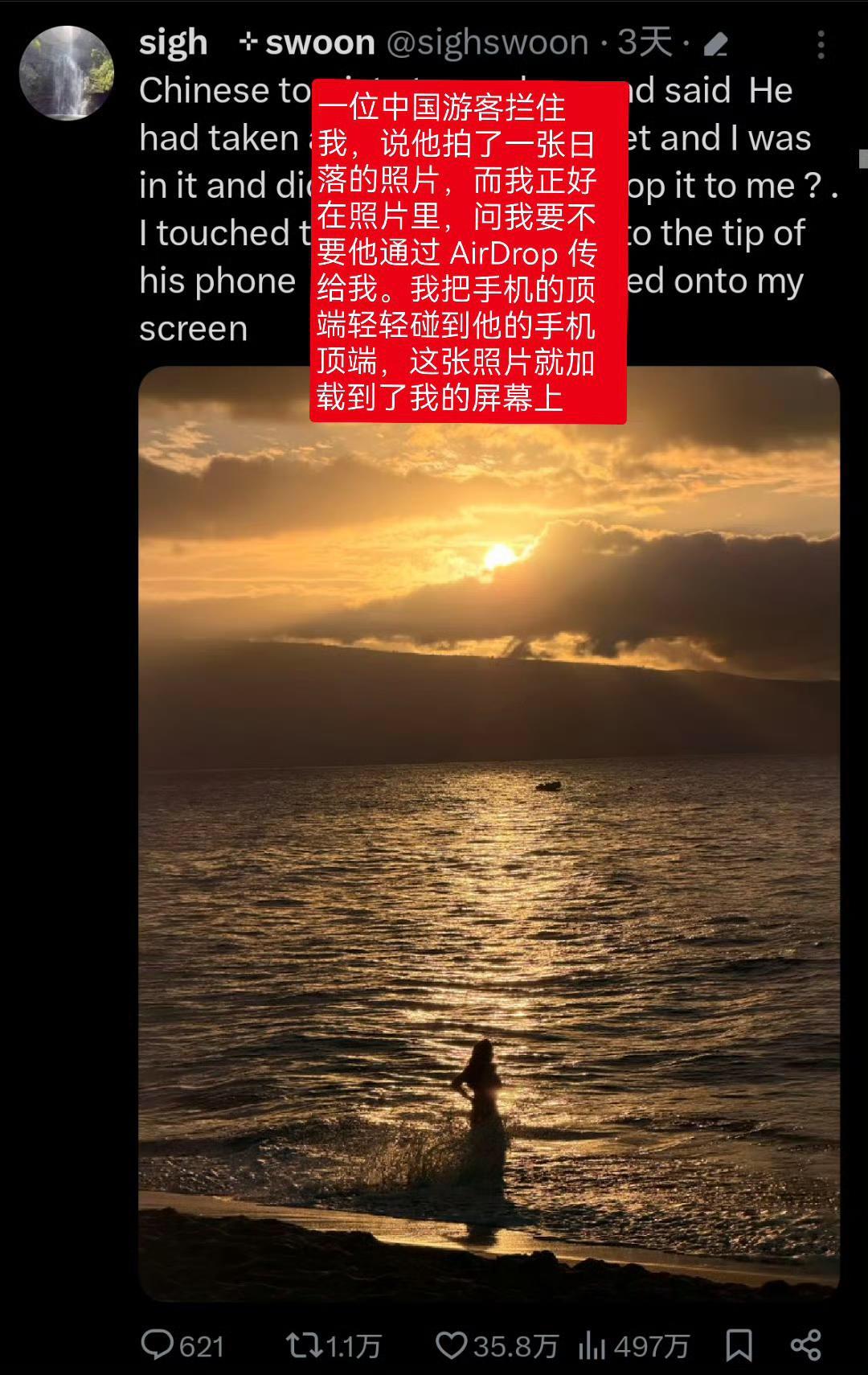1969年的西贡街头,阳光把美国大兵的枪管晒得发烫。 骨瘦如柴的女人弓着背,脸上堆着比哭还难看的笑,任由对方用军靴碾过她刚摆好的水果摊。 路过的人都低着头走,没人敢多看在这个美军吉普比自行车还多的城市,沉默是最安全的活法。 阿龙把烟盒攥得更紧了。 他蹲在街角假装数零钱,眼角的余光却没放过那辆军车的车牌号。 三个月前刚潜入西贡时,他还总下意识摸腰间的枪,现在手指已经习惯了烟草的粗糙触感。 这个叫“阿龙”的卖烟小贩身份,比军装更让他觉得陌生,却也更安全。 1969年的西贡像个塞满破布的抽屉,250万人口里挤着15%的战争难民,黑市交易占了城市经济的四成,正好给像他这样的人留出缝隙。 每天清晨五点,阿龙会准时出现在美军基地附近的路口。 他记得岗哨换班的规律,知道哪个士兵喜欢薄荷烟,哪个士官总在买烟时抱怨上司。 午后的金兰茶摊是情报交换站,穿花衬衫的南越军官喝多了,会拍着桌子骂美军的“少爷兵”,说今晚哪条街要宵禁。 这些话都被阿龙混在烟盒的夹层里,深夜回到贫民区的棚屋,用米汤在报纸边角写下密信。 本来想靠卖烟混口饭吃就行,后来发现每个来买烟的人,都是行走的情报源。 芳就住在隔壁棚屋。 第一次见她时,阿龙刚把省下的半袋米放在她门口,就被她红着眼推了回来。 “我不要可怜。”她说着,围裙上还沾着酒吧的酒渍。 后来阿龙才知道,这个总在深夜悄悄哭的女人,要靠在美军酒吧洗杯子,养活瘫痪的弟弟。 1969年的西贡,37%的女人找不到正经工作,像芳这样的“酒吧女”有两万人,她们的笑容里藏着比烟草还呛人的苦。 有次阿龙看到她把客人给的美元偷偷塞给街头要饭的孩子,忽然觉得手里的情报,比枪还沉。 三月的一个雨夜,阿龙接到紧急暗号。 五个情报员要沿湄公河撤离,他得带路穿过美军的“自由开火区”。 橡皮艇划到河心时,直升机的探照灯突然扫过来,他拽着同伴往芦苇丛里钻,子弹打在水面上溅起的水花,凉得像冬夜的露水。 那天带出来的情报里,有美军弹药库的位置这些信息后来帮北越军队端掉了三个据点,但阿龙总想起那个掉了鞋的情报员,在芦苇里一瘸一拐还紧紧抱着公文包的样子。 春节前的最后一个集日,阿龙的烟摊没摆出来。 他把那支磨得发亮的手枪塞进帆布包,里面还有半包没卖完的薄荷烟。 临走前他在芳的门口放了张字条,画着他家村口那棵大榕树那是他当“小黑”时,抱着妹妹躲轰炸的地方。 棚屋的门没关严,他看见芳正把饭团往围裙里塞,大概又要去给那个要饭的孩子送吃的。 烟摊后来被一个瘸腿的老头占了,美军走后,老头总在摊上摆两包薄荷烟。 芳的酒吧改成了裁缝铺,她教女孩子们做衣服时,会说起那个总蹲在街角数零钱的卖烟小贩。 那些藏在烟盒夹层的情报,和芳藏在围裙里的饭团,都是普通人在乱世里没说出口的倔强。 战争会结束,但这些没写进历史书的细节,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站起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