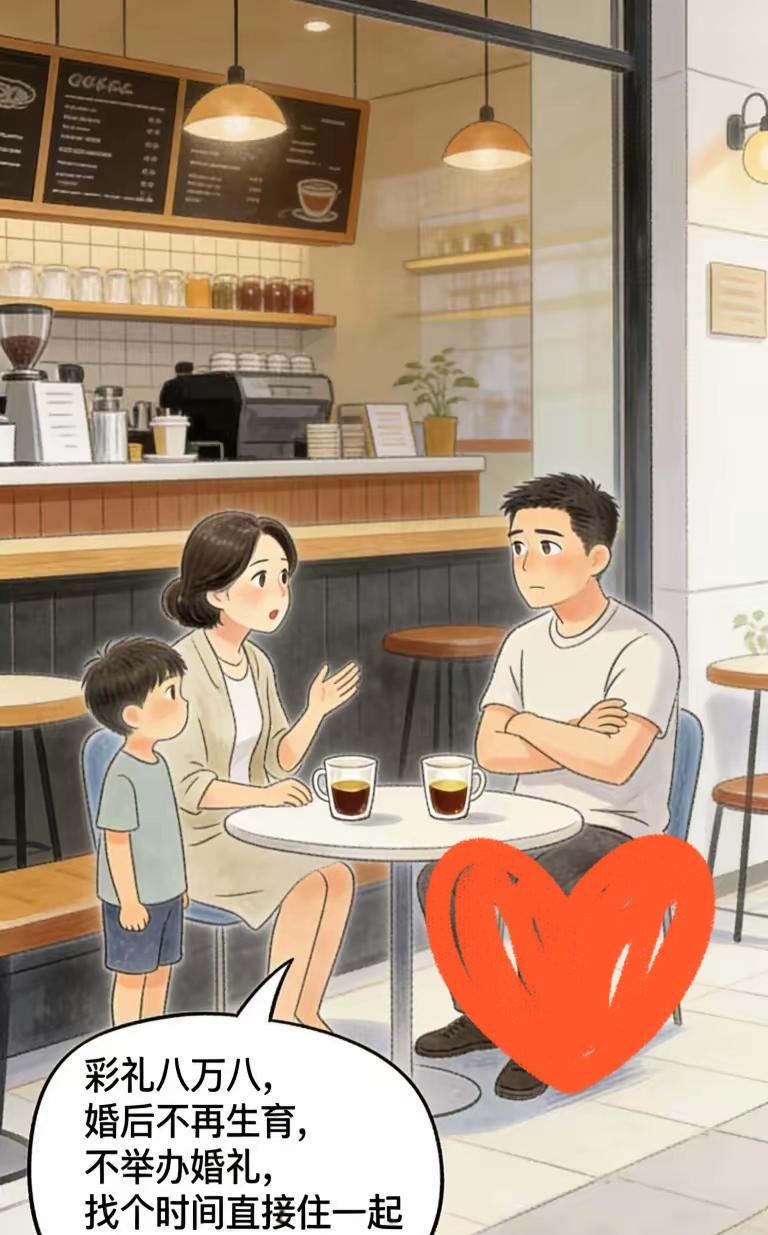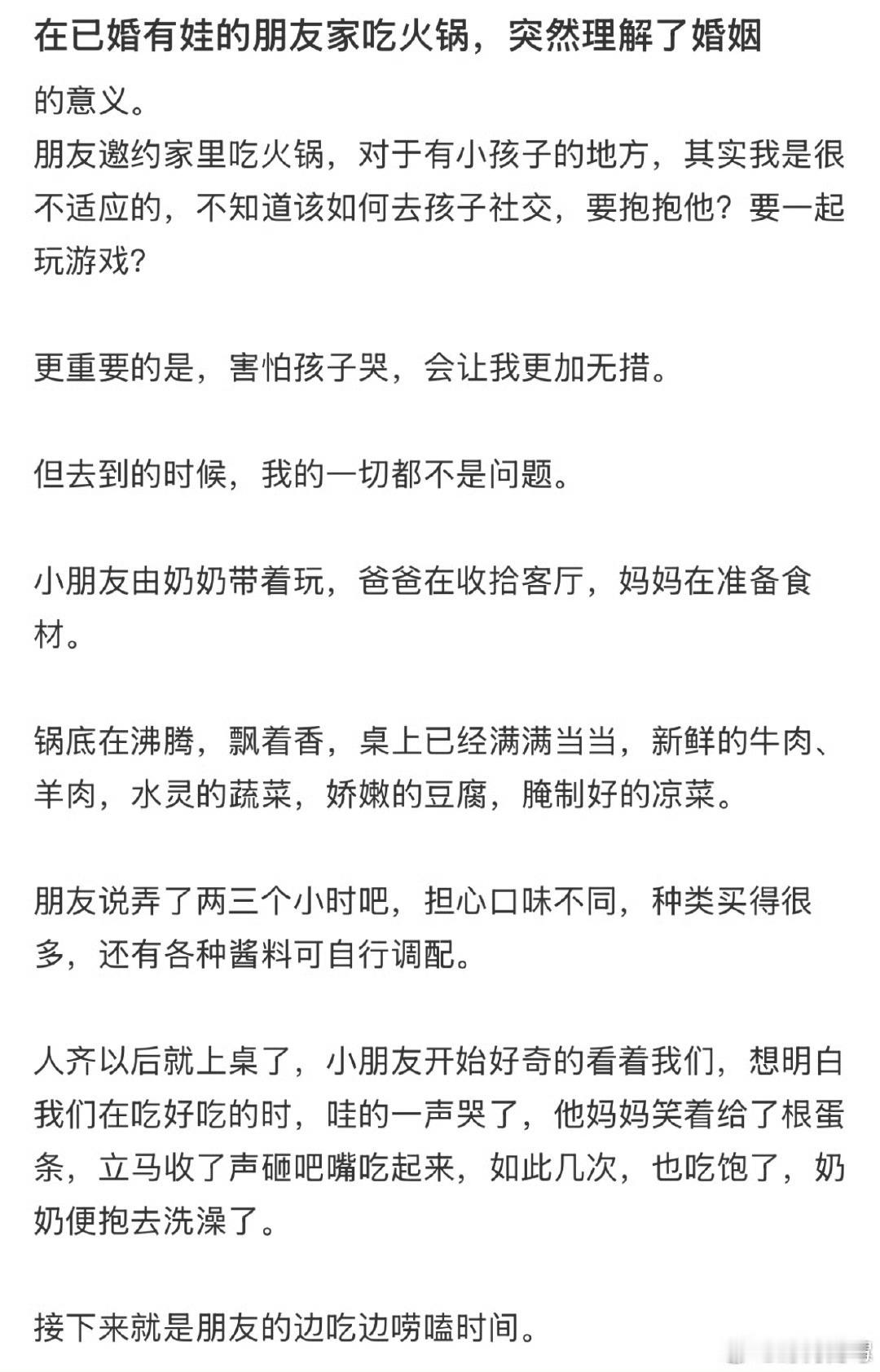这次回老家,遇到一件特别为难的事,到现在都没做好决定。 前一阵,我们回了老公的老家。公婆都不在了。村子里的路修得比去年宽了,可拐到那条熟悉的胡同口,还是一眼就看见公婆留下的老瓦房——墙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黄土,院门口的老槐树还在,枝桠斜斜地伸到屋顶,像个老熟人伸着手要拉我们。 来接我们的是老公的大伯哥,刚进院他就蹲在台阶上抽旱烟,烟圈裹着话飘过来:“弟,弟妹,这次回来,主要想跟你们商量个事——这房子,要不卖了吧。”老公手里的行李箱“咚”地落在地上,我也愣了——这房子是公婆一砖一瓦盖的,老公从出生到上大学都在这儿住,去年公婆走的时候,特意拉着我俩的手说“房子别空着,常回来看看”。 大伯哥看我们愣住,把烟锅在鞋底磕了磕,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你们别多想,我不是图这房子的钱。”他往堂屋走,推开吱呀响的木门,“进来坐,我慢慢说。” 屋里一股潮味,八仙桌蒙着灰,墙上挂着公婆年轻时的黑白照片,玻璃都裂了道缝。老公走到里屋,摸了摸炕沿,那是他小时候写作业的地方,木头都磨得发亮。我知道他心里堵得慌,去年送公婆走的时候,他还在这炕上守了三夜。 “你也知道,”大伯哥坐在板凳上,手指节捏得发白,“我家那小子,今年高三,想考省城的大学,学费生活费不是小数目。我这两年腰不好,在工地也干不动重活了,家里就指着你嫂子种那点地……”他顿了顿,看了眼老公,“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上个月我来扫院子,西厢房的房顶都塌了一小块,下雨漏得厉害,修一次得小两千。我想着,不如卖了,钱你俩拿大头,我拿点给孩子凑学费,也算……没让这房子白占着地。” 老公没说话,从兜里摸出烟,打火机打了三次才着。他平时不抽烟,除非心里有事。“哥,”他猛吸一口,烟从鼻子里喷出来,“爸走那天,拉着我手说,‘这房子是根,你们走再远,回来有个地方落脚’。你忘了?” “我没忘!”大伯哥声音突然高了,眼圈红了,“可根也得浇水啊!你一年回来几次?我隔三差五来拾掇,上个月爬梯子修房檐,差点摔下来,你嫂子吓得半夜睡不着!这房子现在就是个累赘,我守着它,连给孩子凑学费的钱都拿不出,我这当爹的……”他说不下去了,抓起桌上的搪瓷缸子猛灌。 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大伯哥人老实,公婆走后,都是他在照看这房子。去年冬天雪大,他凌晨三点来扫雪,怕房梁压塌,手冻得裂了好几个口子。可这房子对老公来说,不止是房子,是他小时候爬树掏鸟窝、在院子里追着鸡跑、第一次领我回家时公婆在门口笑的样子…… “哥,”我递了张纸巾过去,“卖房子的事,咱先不说。孩子学费差多少?我和你弟先凑上,不够我们再想办法。房子呢,漏了咱就修,钱我们出。你腰不好,别再爬高了,我明天就找镇上的瓦匠来看看。” 老公猛地抬头看我,眼里有点惊讶,又有点松快。大伯哥摆摆手:“那哪行?你们刚买了房,压力也大……” “哥,一家人说啥两家话。”老公掐了烟,走到大伯哥身边,“房子不能卖。爸说的对,这是根。你腰不好,以后修房子的事,我来安排,钱我出。孩子学费,我明天转你卡上,不够再说。”他顿了顿,声音有点哑,“等孩子考上大学,暑假让他来住,我带他爬那棵老槐树,就像小时候爸带我们那样。” 大伯哥愣住了,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就拿手抹了把脸。屋外的老槐树被风一吹,叶子沙沙响,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照在墙上公婆的照片上,好像他们也在笑。 那天下午,我们没再提卖房的事。老公给瓦匠打了电话,约好明天来看房。大伯哥非要留我们吃饭,杀了只自己养的鸡,炖得满屋香。吃饭的时候,他给老公夹了个鸡腿,说:“弟,哥对不住你,刚才说那浑话……” 老公嚼着鸡腿,摇摇头:“哥,该说对不住的是我。以后这房子,咱一起守着。” 现在想想,也不是什么为难事了。房子是根,家人更是根。只要根还在,房子漏了能修,钱不够能挣,可要是把根卖了,就真找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