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的浪轻拍着官船的船舷,一位琉球通事官紧皱眉头,努力模仿着面前老吏的口型。他学的第一个词,不是风雅的问候,而是确保他们一行上百人能安顿下来、吃上热饭的关键。
明嘉靖年间,一艘悬挂着琉球王国旗帜的官船缓缓驶入宁波港。船上的使臣团心事重重——他们需要在此完成复杂的入境手续、交接贡品、接受朝廷查验,然后等待前往北京的许可。然而,一道无形的壁垒比海洋更难跨越:语言。
在严禁民间海外贸易的“海禁”背景下,宁波作为对琉球等国的指定贸易与朝贡口岸,成了少数对外敞开的窗口。踏上这片土地的外国使团,第一门必修课不是四书五经,而是能应付眼前柴米油盐的宁波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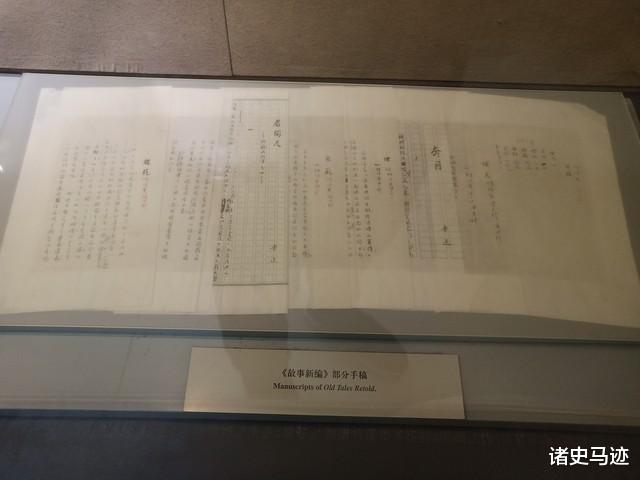
要理解琉球人为何苦学宁波话,得先看看他们面前是怎样一个明朝。
自洪武年间开始,明朝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下海”。这道命令几乎锁死了中国沿海。然而,政策却为像琉球这样“世奉正朔唯谨”的藩属国留下了一道特殊的门缝——朝贡贸易。
在这个体系下,外国使团被允许在指定港口登陆,携带贡品前往京城觐见皇帝,同时也能进行一定规模的官方贸易。而宁波(明州),自唐宋以来就是东方著名大港,在明代被指定为对日本、琉球等国的主要通商口岸。于是,一幅独特的图景出现了:在万里海疆沉寂的背景下,宁波港成为少数几个合法而繁忙的国际枢纽。
所有琉球使团,无论是来进贡、谢恩还是庆贺,他们的船都必须先在这里停靠。在这里,地方官员要查验他们的表文、贡品和人员,安排食宿,并协助他们办理前往北京的全套手续。语言,成了完成这一切前置任务的第一道,也是最实际的关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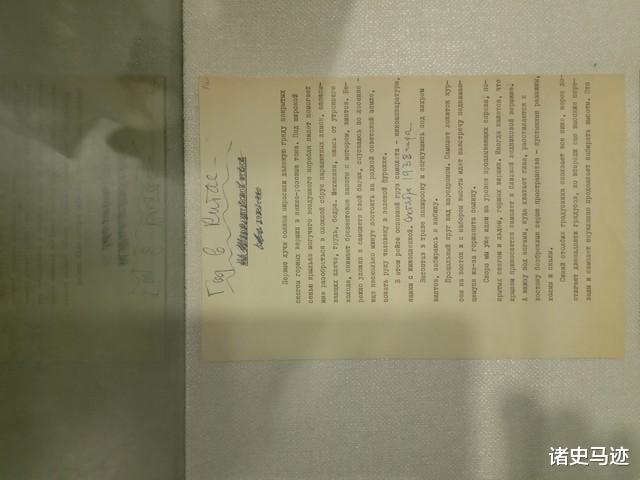
那么,琉球使臣在宁波首先要学什么呢?想象一下他们登陆后的场景。
一个数百人的使团上岸后,需要与市舶司(海关)的官吏沟通,安排住处,采购食物,照料马匹,还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他们随身携带的,或许有从福州“琉球馆”学来的官话教材,但这些课本主要教授的是宫廷礼仪和经史典籍中的雅言。当面对一个宁波的仓吏、驿丞或菜贩时,那些“之乎者也”瞬间失灵。
于是,一些极其务实、充满生活气息的词汇,成了他们迫在眉睫的功课。根据后世对方言的研究,我们可以推测,他们最先听懂的宁波话可能是:
“几钿?”(多少钱?) —— 采购一切生活物资时必须。
“落脚”(住宿)、“饭食”(伙食) —— 向地方接待官员提出最基本需求。
“对牌”(核验凭证)、“关文”(通关文书) —— 办理各种官方手续时的高频词。
“太医”(医生) —— 远航后常有人员病倒,求医问药是常事。
这些词汇无关风雅,直指生存。它们可能由一个略通官话的宁波小吏连比带划地教给使团通事,通事再记录下发音,用琉球语的假名拼命标注。学习的场景可能在码头、在驿馆、在衙门的廊下,充满了焦急与务实的气氛。

在众多穿梭于中琉之间的身影中,有一位宁波人,不仅亲身经历了这种语言隔阂,还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破解历史密码的关键记录。他就是陈侃,明代嘉靖年间的吏科左给事中,一位来自宁波鄞县的官员。
嘉靖十一年(1532年),琉球国王尚真去世,世子尚清请求明朝册封。这项既危险又光荣的使命,落在了陈侃身上。他被任命为册封正使,远渡重洋前往琉球。
与来华的琉球使团一样,陈侃在琉球也面临着语言障碍。作为一位严谨的官员,他在完成册封使命后,撰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使琉球录》。这部书意义非凡,它是现存最早的由明朝册封使撰写的出使全程实录,被收入国家史馆,成为后世研究琉球的权威文献。
更为珍贵的是,陈侃在《使琉球录》的卷末,附上了一张“夷语”(琉球语)词汇表,并用汉字为其注音。由于当时没有标准的注音体系,陈侃在标注发音时,不自觉地带入了自己母语——宁波话的口音。比如,他注音中“加”、“牙”等字的韵母是[a],“世”的读音类似英语的“she”。
数百年后,语言学家通过这些注音反推,惊讶地发现这竟成了研究明代宁波方言语音特点的宝贵资料。一位使臣为解决交流难题所做的朴素记录,无意间为故乡的方言史留下了定格的一瞬。

使团之间的语言沟通,远非简单的词汇替换,背后是两种文化体系的碰撞。清代朝鲜学者李睟光的《芝峯先生集》中,记录了他与琉球使臣蔡坚在北京相遇交谈的细节。蔡坚“能解汉音”,双方可以通过翻译(“译语”)进行基本交流。但当被问及琉球的历史渊源时,蔡坚的回答透露出文献的匮乏:“吾气以前,未有文字,无书籍可记。”
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有时会造成误解,甚至冲突。一份朝鲜史料《燕行录》记载了这样一幕:清朝内务府官员在给琉球使臣分发赏赐的绸缎时,忙中出错,每匹布都被裁短了三尺,还出现了包装标签与内物颜色不符的混乱。耿直的琉球使臣没有忍气吞声,而是选择“呈文礼部”,正式提出抗议。在记录此事的朝鲜使臣看来,这种较真的做法略显“蛮矣”(不懂变通),但这恰恰体现了琉球使臣在长期朝贡交往中形成的、对规则和公正的坚持。
语言的学习,最终导向的是对制度与文化的理解。从学说“几钿”到懂得“呈文礼部”,琉球使臣在宁波学的,远不止方言。

这种跨越海洋的语言学习,其影响是深远的。它首先塑造了琉球王国的上层文化。
自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起,朱元璋应琉球国王之请,“赐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这些来自福建的家族,连同他们的语言、技艺和文化,在琉球扎根,成为中琉交流的桥梁。大量琉球“勤学”来到福州,如饥似渴地学习汉语、儒家经典和各种生产技术。
他们使用的汉语教材,并非标准的北京官话课本,而是由福州先生编写、充满福州方言特色的“官话”读本。在这些《官话问答便语》、《白姓官话》等教材中,出现了大量如“丫霸”(真棒)、“脚手”(手脚)、“闹热”(热闹)等福州方言词汇和语序。因此,有学者指出,历史上琉球人所学的“官话”,很大程度上是一种 “福州官话”。
尽管宁波方言没有像福州话那样系统地进入琉球的教科书,但作为使团踏足中国的第一站,宁波无疑是最直接、最生动的汉语沉浸式课堂。那些在码头、市集、驿站学会的鲜活词汇,构成了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第一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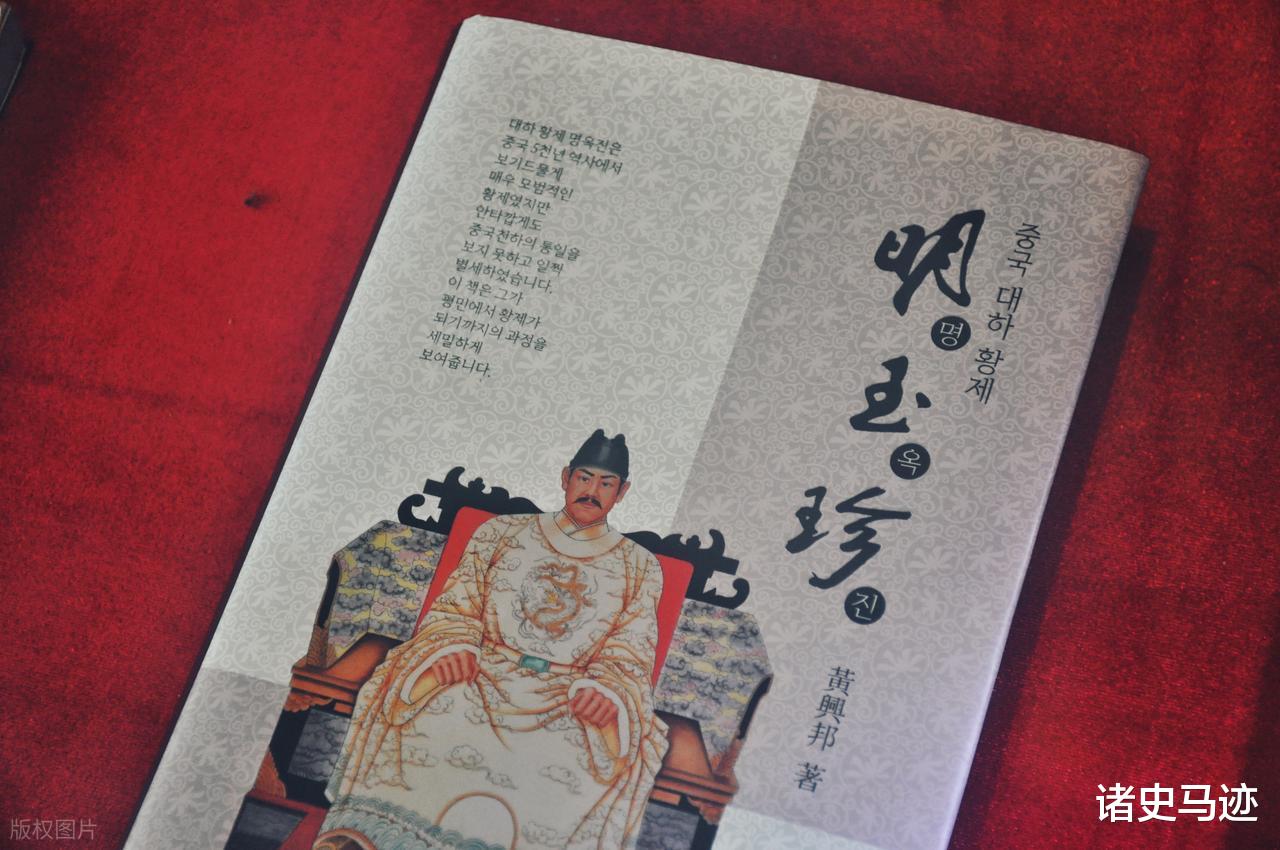
历史的转折总是无情。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琉球王国,设为冲绳县,延续了五百多年的中琉宗藩关系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帝国在冲绳推行严厉的“皇民化”和“国语(日语)教育”。
学校里,孩子们一旦不小心说出琉球语(或方言),就会被挂上“方言札”以示羞辱。日语逐渐取代了琉球语,而琉球士族阶层曾熟练掌握的汉语,也因失去用武之地而迅速凋零。那些曾在宁波港边被反复练习的方言词汇,那些记录在《使琉球录》里的珍贵对音,最终淹没在时代的巨大涛声中,几成绝响。
如今,站在宁波三江口的旧址,已难寻觅当年琉球贡船云集的盛况。但我们可以想象,当那些穿着“倭缎”衣裳、戴着独特冠帽的琉球使臣,揣着刚刚学来的几句生硬的宁波方言,走向市舶司衙门时,他们内心交织着忐忑与希望。
他们最先学会的,不是诗书里的“久仰”,也不是客套的“幸会”,而是能让一行人在异国他乡安身立命的务实之词。这种学习,无关风月,直指生存与使命,却也在这最朴素的层面,完成了文明间最坚实的触碰。
一句消散在历史风中的方言,其重量,不亚于任何宏大的外交辞令。它承载的,是穿越惊涛、维系交往的原始动力,是两个民族在特定历史节点上,为了互相理解而做出的最诚恳、最接地气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