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了两世,皆是为同一人而来。
第一次,他爱我敬我护我,说要与我白首偕老。
这一次,他厌我辱我伤我,恨不能让我不得好死。
好,我便如你所愿。
只是,我说我是她,你为何不信?

1.
夜阑人静,秋雨淅沥。
我跪在永安宫外粗砺的青石板上,膝盖处难忍的痛意早已感觉不到了,只剩麻木。
今日,是我进宫的第一日。
三月前,大萧与戎狄一战中大萧惨烈胜出。
而代价,是我二哥战死,我阿爹重伤。
萧容屿要对我阿爹论功行赏时,我阿爹用谢家的军功换了一个让我进宫的恩典。
犹记得那日阿爹听完我的话后,犹豫再三,才颤着声音开口:
「阿浅,自古武将最受帝王忌惮,你自幼聪慧,该知道若你此时进宫,意味着什么。」
我进宫,会让萧容屿怀疑谢氏别有用心,往大了说,甚至会让他怀疑我阿爹送女儿进宫的目的就是为了颠覆萧氏江山。
可我当时看着我阿爹微白的双鬓,终究还是遂了自己的心意。
我这一世,本就是为了萧容屿而来。
「阿爹,皇上是圣君。」
「阿爹放心,我会护好自己,护好谢家。」
重逢,我已等了许久。
我从落日西斜等到暗月上了柳梢。
可还是没等来萧容屿。
你不来,那我便来找你,可好?
可我进永安宫时,萧容屿只抬头看了我一眼,少年俊朗的面庞一如往昔,只是眸色是我从未见过的冰冷:
「你来找朕,有何事?」
意料之中的态度。
我上前,像我以前常做的那般,挽住他的手臂,终是带了重逢的欣喜和隐隐的期待:
「容屿,我是苏颜。」
萧容屿忽地抬头盯着我,墨色的眼里满是震惊,忽又盛满了怒意,他一把抬起我的下颌:
「谢将军就是这样教导女儿的吗?先皇后的名讳也是你可以唤出口的?」
我一直知,我是萧容屿的禁忌。
不,苏颜一直是萧容屿的禁忌。
如今,我是谢浅。
我还是高估了自己,忘了时移世易,如今我顶着别人的脸,他如何能信如此荒谬之论?
可,终究还是不死心,我真的真的不想哭的,可终究还是带了哽咽:
「容屿,我真的是苏颜,当年的事我也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以为我死了,可一睁开眼,我在将军府,变成了十四岁的谢浅。」
萧容屿静静看着我,他的眼里满是嘲讽和嗤笑:
「荒谬之极,你当朕是三岁孩童吗?」
「看在谢将军于社稷有功,且你年纪尚小,朕不罚你,出去跪足三个时辰,便回自己宫里去。」
他放下手,转过身再不看我一眼,宫灯朦胧,我看到他的背影寂寞清冷,恍若披了一身寒霜。
夜风愈大,落雨逐渐倾盆。
这具娇滴滴的身子何曾受过这般苦楚,再也撑不住。
意识模糊之际,连我都快分不清,苏颜到底是不是我年少时做过的一场绮梦?
若不是,你为何不认我?
你可否知道,那些千回百转的念头,我在心里酝酿了三年,想着见面时再说与你听。
容屿,我真的好想你。
容屿,我真的,是苏颜。
2.
我与萧容屿是青梅竹马,相识于幼时。
他虽为皇子,可自幼身子不好,先帝与我师父是故交,便把他送来燕回山跟着我师父学武。
师父膝下就我和师兄两个徒儿,玩闹惯了,猛然多了一个面若冰霜的孩童,我们初时都是不喜他的。
师父似乎也不喜他,对他总是冷冰冰的,就连看到他的背影,眉头都能蹙成川字,在萧容屿来燕回山之后,师父看向我的时候眼里总是充满悲悯。
我不知为何?难不成是怕我一介小女子被这个高高在上的皇子欺负吗?
不会,师兄和师父会保护我的。
师父不仅武艺高超,还精通各种卜筮命理,且准的不像话。
他不仅教萧容屿剑术,还教他帝王之术,师父很厉害,什么都懂。
师父他总是摸着我的头,说萧容屿的身份尊贵无比,让我别招惹他,离他远点。
可那日,我真不是故意的。
那是初冬。
脉脉花疏天浅,云来去,数枝雪。
我去山间看寒梅忘了时辰,祸不单行,匆忙回去时又崴了脚,我正坐在地上骂骂咧咧,偏在此时遇上了萧容屿。
日渐黄昏,夕光回照,他迎光而立,我第一次发现,他竟如此的好看。
少年眸光淡淡的,看了我良久,才走过来,转身蹲下,冷清的嗓音:
「上来。」
山间万籁俱寂,只余他的脚步声,那么清晰,好像,一下下,踏在了,我的心上。
若不是,我的心,为何跳的那么快?
他背着我走了许久,我嘀嘀咕咕说了好多,他有一搭没一搭的应着。
说了些什么,早已记不清。
只记得,那个夜晚,星光璀璨之极。
后来,我再未欺负过他,他也不知何时起开始唤我阿颜,在看向我时,一贯冷淡的眉眼总是含了笑意。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我有了少女的模样,而萧容屿越发俊朗挺拔,我们还是一起练剑,一起下山历练、一起看繁星点点,一起赏白雪覆原。
直到先帝病重的消息传来,萧容屿第一次跪在我师父面前,我看到他眼中似有万般华彩:
「师父,我想带阿颜回宫。」
师父抬头,像萧容屿初来燕回山那天一般,用怜悯的眼神看向我,似又含了一丝希冀:
「阿颜,你可愿?」

我转头对上萧容屿满含情意的目光,跪在萧容屿身侧,坚定开口:
「师父,我愿意。」
我看到师父起身离去,只是他的手似乎在微微颤抖,他认命般闭了闭眼,他说罢了。
先皇驾崩,萧容屿即位,我做了他的妻,他要封我做皇后,可朝堂异声四起,说我一乡野女子不可堪一国之母。
萧容屿发了好大的脾气,他把我揉进怀里,眼里满是愧色:
「阿颜,是我对不住你。」
「难道我跟你回京是为了皇后虚名吗?那你未必太小瞧我了,我只想,做你的妻。」
萧容屿在朝堂上是杀伐决断的帝王,但私下我们却像寻常夫妻般相处,他为我挽发描眉,我为他吟诗唱曲,我们一起月下练剑,像少时那般,他从不让我唤他皇上。
我以为岁月能一直这样下去。
可我十八岁生辰那日,萧容屿知我山野待惯了,不喜皇宫,说要带我出宫散心,我们着了常服,却不想遇上刺客。
萧容屿在燕回山十数载,一回宫就继承了皇位,让宫中其他皇子情何以堪,自是嫉恨至极。
我们都有武艺在身,可对方人多,终究是寡不敌众。
我们落了下风,他只一心护着我,肩头已被刺伤,又有一把冷刃冲着他而来,直指心肺,可他分身乏术,我推开他,替他挡住了,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看到萧容屿的人赶来了。
他接住我下坠的身体,随我跌坐在地上,眼里是我从未见过的痛苦绝望,他一遍遍唤着阿颜,我想回应,却再说不出一句话来。
终究,他没事便好。
我以为我死了,可我再次醒来是在谢府,铜镜中映出陌生的脸,恍惚了好久,我才接受我又活过来的事实。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我想,这是老天给我的第二次机会。
我死了,听闻萧容屿将我尸身放入帝陵,百年后要与我合葬。
听闻他立我为后,再不顾忌朝中大臣的反对。
听闻他昭告天下,国母逝,举国同悲,五年不选秀。
如今是第三年,我用谢家的军功换了我进宫的机会。
可他,不信我。
3.
膝盖处针刺般的痛,如意一遍遍替我敷着腿上的淤青。
她是我从谢府带来的。
从那晚罚跪过后,我再未见过萧容屿。
但我并未太过介怀,重生言论,本就太过荒谬,只怕他以为这是我邀宠的手段。
便,慢慢来吧。
灯光微漾,我伏在案前,一笔一画皆倾注了情义,落于宣纸上。
萧容屿曾说,见字如见人,他能用字迹来识人,甚至能辩我落笔时的心神。
或爱、或恼、或怒,或思念,我不信,曾试过,皆准的离谱。
既如此,你可否会认出我?
我让如意拿着我的信函,去了永安宫。
她是戌时去的,我站在院中等了足足一夜,直到晨光微现。
秋风萧瑟,桂花瓣飘飘洒洒,在院中铺了薄薄的一层。
萧容屿才姗姗来迟。
他漆黑的眸子冻结了寒冰,脸上却疲态尽显,显然也是一夜未眠。
如意,如意是被两个侍卫拖进来的,手指上血迹斑斑,红肿不堪。
她看到我,眼中忽然蓄满了泪,一句句念着小姐,小姐。
我看向萧容屿,想问这是为何?
他却先一步开口,看向我的眼里是丝毫不加掩饰的厌恶:
「倒是朕小瞧你了,你的婢女已招认了,你在十四岁前写的一直是簪花小楷,你说,练这一手字,费了多少功夫?」
他拿着我的信纸,扬起来甩在我的脸上,眸色深沉似海:
「朕不管你入宫的目的,但我警告你,永远不要再拿你和朕的妻子相提并论,你不配。」
他说,我不配。
我抚上他的手:
「容屿,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为何不信我?」
他嫌恶甩开我的手,转身冷声对着侍卫吩咐:
「动手。」
我看到他们把如意压倒在长凳上。
我慌了,匆忙走到萧容屿面前:
「你要做什么?」
「你的婢女以下犯上,朕如今,难道连处置一个宫人也要经过你的同意吗?」
棍棒落下,如意凄惨的叫声传入我的耳中,她是因我,才受这无妄之灾。
棍棒落在她背上,是冲要她命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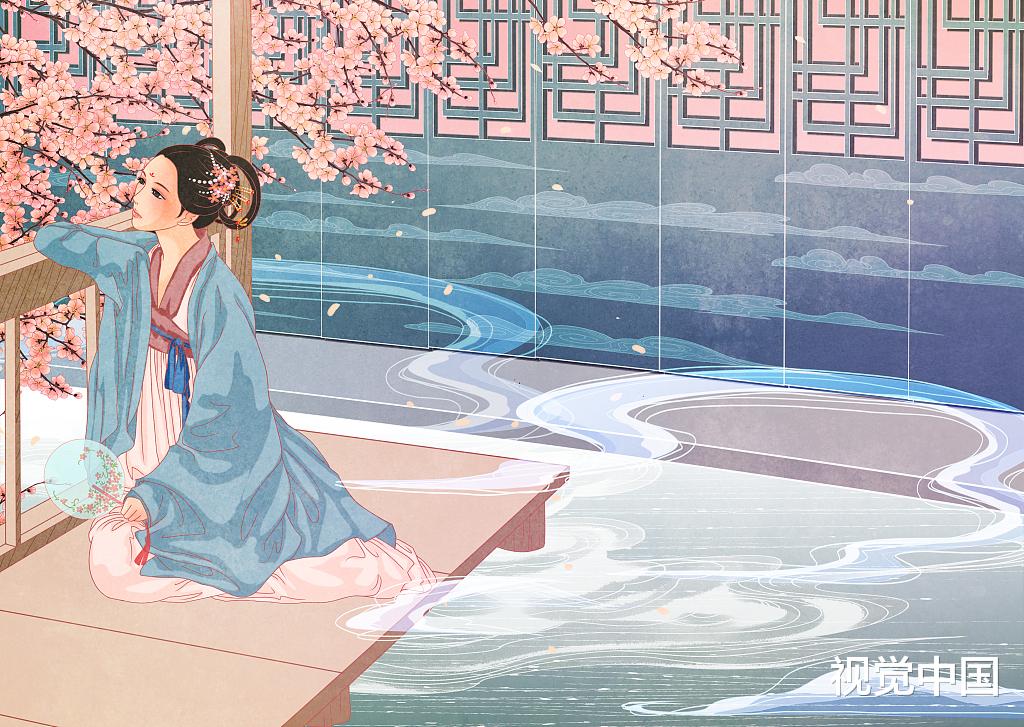
我慌忙拉住萧容屿的袖子,恳求道:
「你先让他们住手,字的事我可以解释,你不是说字迹可辩人心,为何你不信我?我真的没有骗你。」
萧容屿眸色深沉如海,可还是冷冷看着侍卫行刑,我看到如意的嘴角流出鲜血,再喊不出一声。
师父说过,人生来平等,萧容屿是认同的,可他如今,朝一个无辜的婢女发泄着他的怒火。
「萧容屿,为何要将怒火撒在一个下人身上,视人命如草芥是一个圣君可为之事吗?你恨我,那你有本事冲我来。」
他似是愣了一瞬,才一耳光扇在我的脸上:
「放肆。」
「你是不是赌朕不敢杀了你?」
可明明是你说的,不让我喊你皇上。
为何,不作数?
我擦去嘴角的血迹,也冷冷看他:
「你敢杀了我吗?我是谢氏女,我二哥沙场为国死,马革裹尸还,你若不怕寒了朝中老臣的心,你就杀了我。」
他嘴角扯出一个嘲讽的笑,眼睛却冰寒无比:
「谢氏女?怎么?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