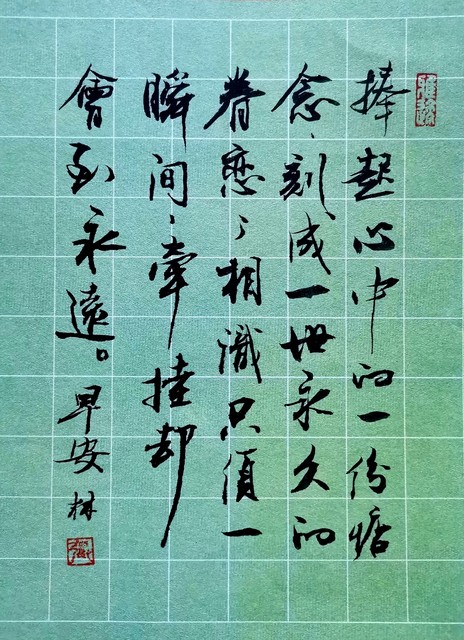作者:吴钩随笔
你还记得课本里的那只大鹏吗?
背若泰山,一飞九万里;对比之下,只会在树枝间跳来跳去的小鸟,显得可笑又局促。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庄子》的印象就停在这里:想象奇特,却离生活很远。
直到今年八月,我和几位老朋友约着一起读《庄子》,才发现自己以前,看得实在太浅。
 一、茶话会里的《庄子》:从大鹏到“此心”
一、茶话会里的《庄子》:从大鹏到“此心”我们约在一个安静的小空间。
每次聚会,都从集体朗读开始:先读原文,再对照几种不同的译本,然后一段一段讨论,谁有感想,谁就开口。
几个月下来,我们读完了《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下一篇是《人间世》。
读《逍遥游》,我才真正明白: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一个人若总是被“我是谁”“我有多厉害”“别人怎么看我”牵着走,他的精神就永远飞不起来。
真正的“逍遥”,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完全活在名利得失里。
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庄子,离我们的日常,其实并不遥远。
 二、《齐物论》:是非太响,“道”就听不见了
二、《齐物论》:是非太响,“道”就听不见了印象最深的,是《齐物论》。
开篇,庄子分了三种“籁”:人籁、地籁、天籁。
人籁,是人的声音。喜欢区分:你和我,是与非,利与害。
我们太熟悉这种状态了:
一则新闻,评论区立刻站队;一件小事,非要争个谁对谁错;社交媒体上,不断有人喊:“你必须表个态!”
庄子说: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
事情还没弄明白,心里就迫不及待贴上“对”“错”的标签,就像今天才动身去越国,却说昨天就到了。
古人讲“四重境界”:
最高是“未始有物”,万物未分;其次是“有物未始有封”,虽有万物,未有疆界;再其次“有封未始有是非”,有界限,但不急于判断;最后,才是“是非之彰”。而当“是非”过度彰显时,“道”就开始被遮蔽了。
因为一旦陷入争辩,我们看的就不再是事物本身,而是自己的立场、情绪和胜负欲。
庄子有一句话,特别像在对今天的人说:
“辩也者,有不见也。”
越想赢,越看不见。越要分黑白,越远离那条更大的“道”。
 三、《养生主》:庖丁的刀,是顺着“道”在走
三、《养生主》:庖丁的刀,是顺着“道”在走《养生主》篇幅不长,却极为精妙。
最有名的,就是庖丁解牛。
他对文惠君说: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刚开始,他和普通人一样,只见“全牛”;后来慢慢熟悉筋骨结构,再到最后
“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眼不再刻意看,手不再刻意算计,整个人与“牛的结构”合在一起。
他下刀,只顺着牛体的纹理与缝隙走:
“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
于是,刀用十九年仍然锋利如初。
庄子借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件事:
真正高明的,不是硬碰硬,而是顺着规律走。
养生如此,做人做事亦如此。
我们常常太用力:身体累了还拼命扛,关系僵了还非要争最后一句,明知不合适的路,还不肯回头。
结果,不但事难成,人也先折损了。
“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
沿着经络走,而不是乱撞;沿着事物的“筋骨”走,而不是一味硬切,人才能保身、全生、养亲、尽年。
这就是庄子眼中的“养生”:不是补品和方子,而是学会在生活里,不和“道”较劲。
 四、安时处顺:看轻一点生死,也看轻一点得失
四、安时处顺:看轻一点生死,也看轻一点得失《养生主》里,还有一段关于老聃之死。
老聃去世,一个叫秦失的人前去吊唁。他只哭了三声,就走了。
弟子们非常不满:“老师生前那样看重你,你怎么这么无情?”
秦失淡淡地说: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来,是顺着这个“时机”来了;走,是顺着这个“时势”去了。
他不是没有悲伤,只是把生死,看在“时”的流转中,而不是只看在个人的爱憎得失里。
这种态度,也可以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
事业有起伏,看它是“时势变化”,不是“世界亏待了我”;关系有聚散,看它是“缘分到了”,不是“谁必须负责”。不是叫你冷漠,而是让我们多一点顺势的心,少一点钻牛角尖的执。
“安时而处顺”,既是养生之道,也是安身立命之道。
 五、读《庄子》,是学会给自己“松一松”
五、读《庄子》,是学会给自己“松一松”这些日子读下来,我越来越觉得——
庄子不是要我们逃避世界,而是提醒:
别被“对错”“输赢”“成败”压得透不过气。
当我们不再急着给一件事、一个人、甚至给自己下结论,那条“道”的细线,就会慢慢显现。
我们可以:
在争吵前,先停一停,不急着判断谁对谁错;在受挫时,问问自己:是不是一直在“硬砍”,而没有顺着事物的纹理走?在人生的得失中,试着多看一点“时”,少纠缠一点“我”。庄子说:
“天地一指,万物一马,道通为一。”
站得高一点,很多非黑即白的执念,其实都可以放下。

读《庄子》,像是在心里打开了一扇小小的天窗。
风一吹进来,旧有的是非成见,就松动了一些。
也许我们做不到“至人无己”,做不到“哀乐不入”,但至少可以给自己一个新的选择:
不再急着分黑白,也不再忙着给人生判决。
这样走下去,或许就离那条“道”,近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