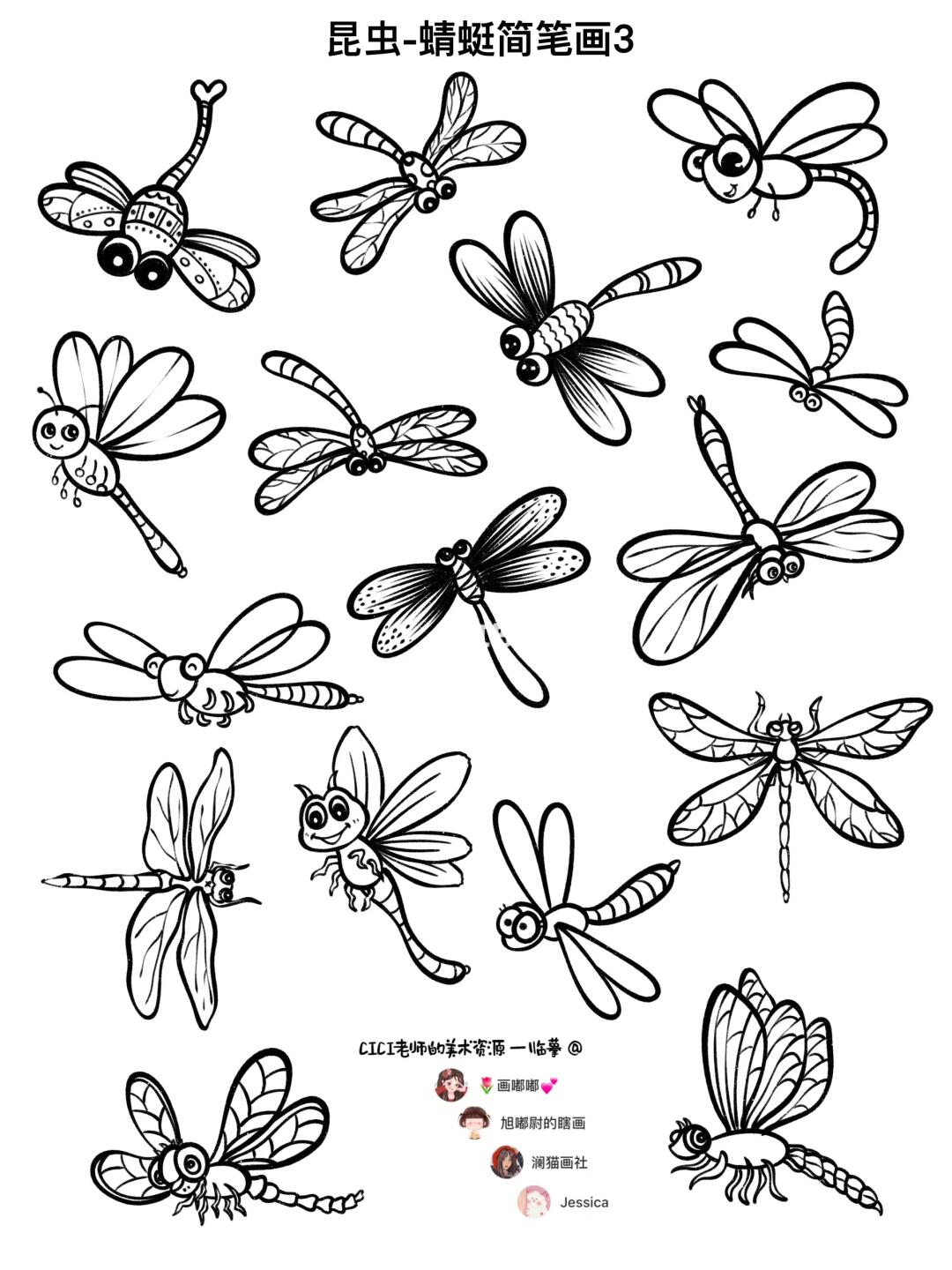凌晨两点,医院打来电话。
我爸突发心梗,手术要先交六万。
我卡里只剩四万三,刚赔了一百多万投资。
弟弟苏文强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姐,你年薪百万,六万不就是顿饭钱吗?”
我借钱凑齐了手术费。
我爸出院那天,说要去弟弟家住。
弟媳赵晓芳脸都绿了:“我们家哪还有地方?”
我爸拿出存折:“我退休金四千八,每月给你们三千,当房租饭钱。”
我愣住了。
这些年我给他转的钱,他转头都贴给了弟弟......
01
手机屏幕在深夜两点亮起的时候,我正在核对一份漏洞百出的投资报表。
那是个陌生号码,区号显示老家。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指悬在接听键上三秒,才滑开。
“请问是苏文娟女士吗?这里是市第一人民医院,您父亲苏建国突发心梗,需要立即手术,请您尽快赶来。”
护士的声音公式化得像自动播报,可每个字都像冰锥扎进耳朵。
我张了张嘴,喉咙发紧,半天才挤出一句:“手术费……要多少?”
“先准备六万,多退少补。”
六万。
我下意识点开手机银行,余额显示:四万三千八百二十六块五毛。
这个数字让我胃里一阵抽搐。
年薪一百二十万听起来像句笑话——去年跟风投资跨境电商,踩中平台暴雷,一百多万本金打了水漂不说,还欠了朋友三十万应急债。
现在这四万存款,是我上个月项目奖金刚到的钱。
窗外的上海下着黏腻的雨,雨水顺着高楼玻璃扭曲滑落,像哭花的脸。
我抓了件外套冲出公寓,一边叫车一边拨弟弟苏文强的电话。
响了七声他才接,背景音是麻将碰撞的哗啦声和女人的尖笑。
“姐?这么晚了……”
“爸心梗住院,要六万手术费,你现在带钱去医院。”
我的声音冷静得自己都害怕。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麻将声停了。
“六万?我……我手头哪来这么多现金啊。”
苏文强声音压低,“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小破公司上半年亏了多少,房贷车贷都快还不上了……”
“苏文强。”
我打断他,“上个月爸跟我说,你刚换了台二十万的新车。”
“那是贷款买的!零首付!”他急了,“姐,你年薪一百多万,六万对你来说不就是顿饭钱吗?你先垫上,等爸医保报销下来就还你。”
我闭上眼睛,指甲掐进掌心。
又是这句话。
这些年我听了无数遍的“你先垫上”。
垫首付,垫彩礼,垫侄女的早教学费,垫他公司“周转”。
每一次的“垫”都成了沉没成本,连个水花都没见过。
出租车在凌晨的街道上飞驰,雨刮器来回划着弧线。
我又拨通了好友林薇的电话。
她是唯一知道我投资惨败的人。
“薇,借我两万,急用。”
我没废话。
林薇在睡梦中惊醒,却二话没说:“账号发我,五分钟到账。”
顿了顿又说,“文娟,这次又是家里的事?”
我没回答,挂了电话。
两分钟后,银行短信进来:20000.00元已到账。
我盯着那串数字,眼眶突然烫得厉害。
赶到老家医院时,天刚蒙蒙亮。
父亲已经推进手术室,走廊长椅上坐着弟弟苏文强和他老婆赵晓芳。
赵晓芳正低头刷手机,屏幕上闪动着购物直播的红包弹窗。
苏文强看见我,立刻站起来,脸上堆出愁苦的表情:“姐,你可算来了,医生说要马上交钱才能动刀……”
我把银行卡递给他:“密码爸生日,里面有六万三,你去交。”
他接过卡,动作快得像怕我反悔。
赵晓芳这才抬起头,扯出个笑:“姐真是能干,这么大事儿说解决就解决了。”
她手腕上那条卡地亚手链晃着光,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三万八。
当时她说:“姐对我比亲姐还好。”
02
手术很顺利。
父亲在ICU躺了两天转入普通病房。
这七天我请了年假,白天陪护,晚上在医院附近小旅馆凑合。
苏文强夫妇每天下午“打卡”一样出现,拎点水果,坐半小时,话题总绕不过“钱”。
“姐,爸这后期康复听说挺烧钱的。”
第七天下午,赵晓芳削着苹果,状似无意地说,“请护工一天三百,营养针一支五百,我们打听过了……”
“医保能报一部分。”
我盯着心电图仪上跳动的绿线。
“那自费部分也不少啊。”
苏文强接话,“我和晓芳商量了,我们出人出力,白天夜里轮流照顾,这辛苦钱就不算了,但药费营养费……”
“该平摊的平摊。”
我说。
病房里突然安静。
父亲咳嗽了一声,慢慢睁开眼睛。
他看看我,又看看苏文强,喉咙里发出含糊的声音。
我俯身去听。
他说的是:“文强……难……”
心像被钝器砸了一下。
又是这样。
从小到大,只要我和弟弟有冲突,父亲永远先说“文强难”。
因为他学习差,因为他工作不顺,因为他“不如姐姐能干”。
能干成了我的原罪。
父亲出院前一天,主治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
“苏小姐,你父亲这种情况,出院后需要静养至少三个月,环境要安静,情绪要平稳。”
医生推了推眼镜,“最好有专人照顾,定期复查。”
我点点头:“我会安排。”
回病房的路上,手机震动,是公司合伙人发来的微信:“文娟,深圳那个项目黄了,投资方撤资,我们垫进去的八十万可能打水漂。”
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闭上眼。
八十万。
那是我抵押了上海公寓才凑出的最后筹码。
现在,它也要没了。
推开病房门时,父亲正坐在床边,苏文强和赵晓芳一左一右站着,气氛有些微妙。
“爸,出院后您先跟我回上海住一阵吧。”
我尽量让声音平稳,“我租的房子虽然小,但安静,适合休养。”
父亲摇摇头,动作很慢,却异常坚决:“我去文强家。”
我愣住了。
赵晓芳脸色一变:“爸,我们家那两室一厅,婷婷占一间,我们占一间,您去了睡哪儿啊?”
“客厅沙发就行。”
父亲看着苏文强,“你小时候发烧,我抱着你在客厅坐了一夜,也没嫌沙发硬。”
苏文强嘴角抽了抽,瞪了赵晓芳一眼,转头对父亲挤出笑:“爸愿意来住当然好,就是怕我们照顾不周……”
“不用你们照顾。”
父亲打断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个破旧的存折,“我有退休金,一个月四千八,够我吃喝。”
他抬起头,目光第一次直直看向我:“文娟,你的钱,我一分不要。”
空气凝固了。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撞在铁皮鼓上。
“爸,您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的赡养费,我不收了。”
父亲把存折塞回枕头下,动作带着某种仪式感,“你弟不容易,我得帮帮他。”
赵晓芳眼睛一亮:“爸,您要贴补我们?”
“一个月三千。”
父亲说,“我留一千八零花,剩下三千给你们,就当我的房租饭钱。”
我站在那里,像被人扒光了扔在冰天雪地里。
三千。
我忽然想起很多细节——父亲总说退休金“刚够用”,却每次见我都要念叨“你弟手紧”;赵晓芳朋友圈里隔三差五的网红餐厅打卡;苏文强那辆越换越贵的车。
原来我这些年拼命往上爬的时候,父亲正拿着我逢年过节塞给他的红包,一笔笔转交给他的儿子。
而我还在自责给得不够多。
03
“爸。”
我的声音飘忽得像不是我自己的,“您知道我刚赔了一百多万吗?”
父亲皱眉:“你投资失败是你的事,文强可是实打实要养一家三口。”
“所以我就活该?”
我终于吼了出来,七年来的委屈像火山喷发,“我活该一个人在上海熬夜加班,活该被投资人指着鼻子骂,活该欠一屁股债还要装成功人士,就为了你们一句‘我姐有钱’?!”
苏文强跳起来:“苏文娟你怎么跟爸说话的!”
“我怎么说话?!”
我转身揪住他衣领,这个比我高半头的男人竟被我拽得踉跄,“苏文强,你结婚我出二十万,你买房我出三十万,你女儿上国际幼儿园我出八年学费,你现在告诉我,爸一个月贴你三千?那我算什么?你们全家的提款机?!”
赵晓芳冲过来扯我的手:“姐你疯了!松开!”
“我是疯了!”
我甩开她,眼泪终于决堤,“我被你们逼疯的!”
父亲重重拍床板:“够了!”
他喘着粗气,脸色发青:“文娟,你要是不满,以后不用回来了。我有儿子养老,用不着你操心。”
我看着他那张苍老而固执的脸,忽然觉得无比陌生。
这就是我拼尽全力孝顺了三十八年的父亲。
在他心里,女儿再能干也是外人,儿子再窝囊也是根。
多可笑。
我后退一步,擦掉眼泪,从包里掏出钱包,抽出仅剩的三张百元钞票,轻轻放在床头柜上。
“这三百,给爸买点营养品。”
我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从今天起,我不会再给这个家一分钱。至于爸要住哪儿,贴补谁,随您高兴。”
我看向苏文强,笑了笑:“弟弟,恭喜你,终于得偿所愿,成了爸唯一的依靠。”
转身离开时,赵晓芳在身后尖声说:“苏文娟你别后悔!”
我没回头。
走廊很长,灯光惨白,我的影子在地上拉得扭曲变形。
走到医院大门口,阳光刺眼,我戴上墨镜,叫了辆出租车。
司机问去哪儿。
我说:“火车站。”
车子启动的瞬间,我最后看了一眼医院大楼。
父亲应该正被儿子儿媳簇拥着,享受着他用偏心换来的“天伦之乐”。
而他不知道,或者说不在乎——他的女儿,此刻口袋里只剩二十三块五毛,连一张回上海的高铁票,都是临时用花呗买的。
回到上海的那一周,我把自己埋进工作里。
白天跑投资人,晚上改方案,困了就在办公室沙发上眯三小时。
合伙人看我的眼神充满担忧:“文娟,要不你先休息几天?”
我摇头:“八十万的窟窿填不上,我睡不着。”
第八天深夜,我收到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姐,爸真的住进来了,客厅沙发都给他铺好了。他说以后每个月一号给我们三千,让我们好好孝顺他。”
是赵晓芳。
我没回。
三分钟后她又发:“其实爸心里还是疼你的,就是嘴上硬。”
我直接拉黑了号码。
父亲的退休金转账记录,是我在第二个月偶然发现的。
那天我鬼使神差地点开手机银行,查看往年给父亲的转账记录——每年春节五万,生日两万,平时杂七杂八加起来也有三四万。
而最新一条记录显示:两个月前,父亲账户有一笔三千元的转出,收款人:苏文强。
时间正好是他出院后的第一个月。
他真的说到做到。
我关掉手机,走到窗前。
上海的夜空很少有星星,今晚却意外地能看到几颗,冷冷地挂在天上,像嘲弄的眼睛。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我和弟弟去乡下看星星。
他把我扛在肩上,指着银河说:“文娟你看,那像不像一条发光的河?”
弟弟在下面哭闹,父亲只好把我放下来去抱他。
我那时七岁,已经学会说:“爸,你先哄弟弟,我自己看。”
父亲摸摸我的头:“还是文娟懂事。”
懂事。
这个词绑架了我三十年。
现在,我不想懂了。
04
日子流水一样过去。
我搬出了月租八千的公寓,在公司附近租了个三十平的单间。
八十万的窟窿填上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我和合伙人签了对赌协议——明年这个时候,如果项目利润达不到三百万,我净身出户。
签协议那天,林薇气得骂我:“苏文娟你疯了?那是你最后的退路!”
我笑:“我早就没有退路了。”
第三个月的一个周六早上,门铃狂响。
我从一堆设计稿里爬起来,迷迷糊糊开门,门外站着赵晓芳。
她头发凌乱,眼睛红肿,身上那件香奈儿外套皱得像腌菜,完全没了往日的精致。
看见我,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指甲掐进我肉里。
“姐!救命啊!老爷子疯了!”
我怔住。
她语无伦次,眼泪鼻涕一起流:“爸他……他把我们家客厅改成棋牌室了!上星期叫了四个老头天天打麻将,抽烟喝酒,半夜都不散!婷婷被吵得天天哭,我跟你弟说他还不听,说那是他爸,爱怎么住怎么住!”
她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现在好了,今天早上爸说要收那些老头台费,一桌抽两百,说是贴补家用……邻居都报警了!姐,我求你了,你去把爸接走吧,我们真受不了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狼狈的模样,心里涌起一股荒唐的寒意。
三个月前,父亲信誓旦旦说“有儿子养老”。
三个月后,他儿子的老婆跑来哭诉“老爷子疯了”。
而这一切,似乎早在那个雨夜的手术室外,就已埋下伏笔。
我慢慢蹲下身,看着赵晓芳的眼睛。
“晓芳。”
我说,“爸不是疯了。”
“他是故意的。”
赵晓芳的哭声戛然而止。
她抬头看我,瞳孔里映出我平静到近乎冷酷的脸。
远处传来电梯到达的叮咚声,走廊尽头的窗户漏进一缕惨白的晨光。
新的一天开始了。
而我知道,有些账,终于到了要算清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