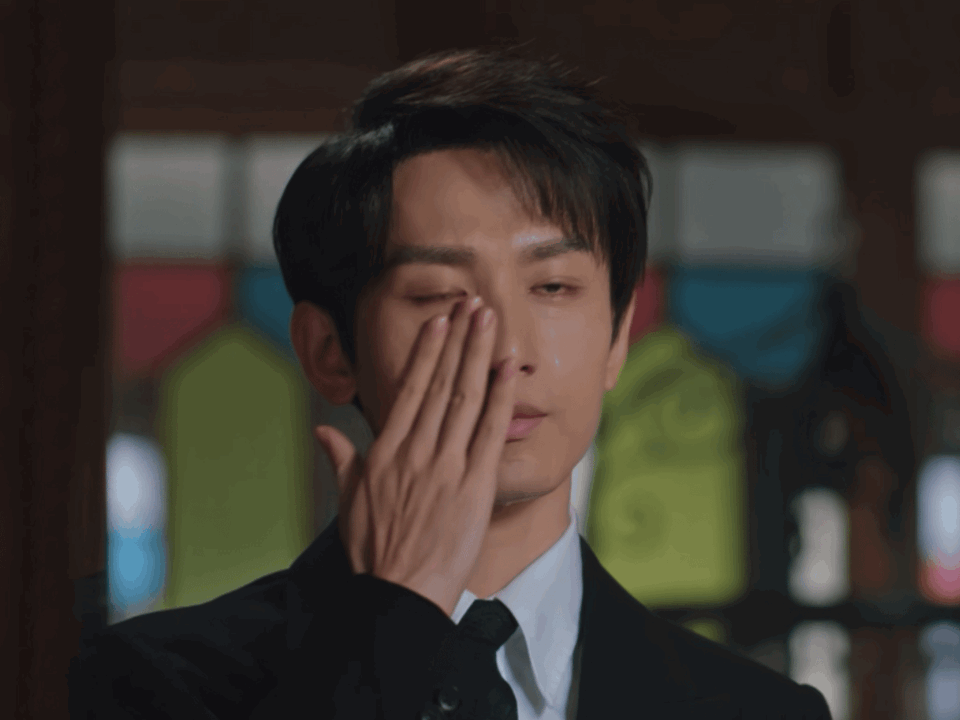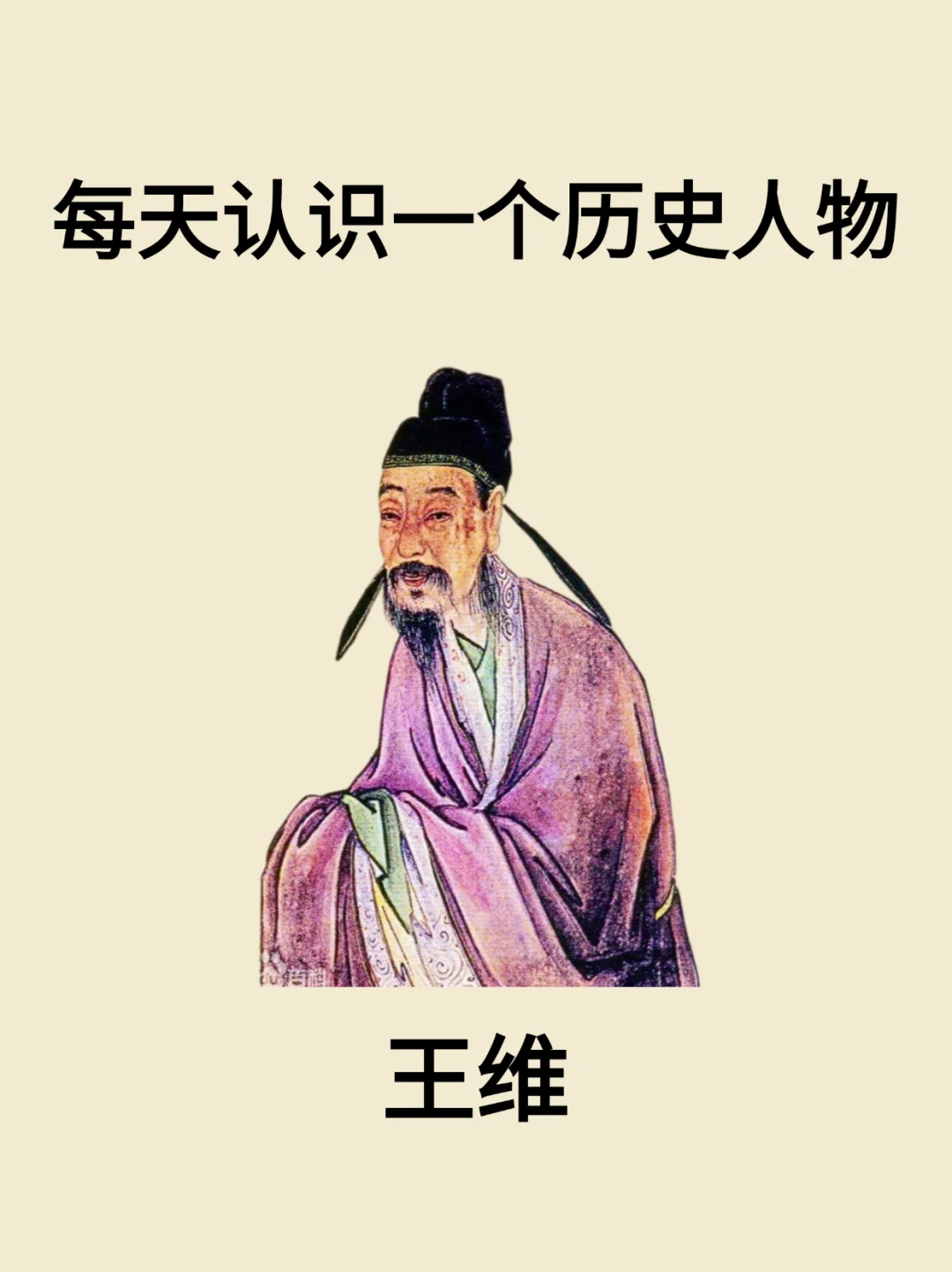我爸生意破产,欠了100多万外债,除夕夜他拎着老鼠药,说要全家一起走。
我和妈妈假装顺从,提议不如去水库,走得“体面”点。
他感动得痛哭流涕,说下辈子还做一家人。
水库边,他紧紧搂着我们,一步步走向深水,嘴里念叨着“共进退”。
就在水没过他腰际的瞬间,我和妈妈对视一眼,默契地同时发力。
他惊愕的表情被翻滚的河水吞没前,似乎想说些什么。
我和妈妈浑身湿透爬上岸,没人说话,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从那一刻起彻底变了。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几天后整理遗物时,我在他抽屉夹层里发现了一张孕检单,日期就在他破产前。
而单子背面,用铅笔写着一个陌生的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
我顺着号码查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柔弱的女人,然而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浑身的血都凉了。
01
周振国的生意破产了,欠下了一百多万的债。
那笔债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得我们家透不过气来。
他开始酗酒,整夜整夜不回家,偶尔回来,也是满身烟酒气,眼神浑浊。
我和母亲苏慧沉默地看着这一切,像两个等待宣判的囚徒。
除夕那晚,外面烟花炸响,我们家却冷得像冰窖。
周振国灌下半瓶白酒,突然把瓶子狠狠摔在地上,玻璃渣飞溅。
“完了,全完了。”他红着眼睛,盯着我和苏慧,“活着也是拖累,不如一家人整整齐齐走了算了,我搞了点东西。”
他说的是老鼠药,就放在门口的鞋柜上。
那一刻,空气都凝固了。
我看着母亲颤抖的手,心脏像被攥紧了。
“爸。”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异常平静,“老鼠药死得太难看了,肚子疼,还会吐得到处都是。要真是想走,合金水库那边水够深,也干净。”
周振国愣住了,似乎没想到我会接话。
苏慧猛地抬起头看我,眼眶通红,但她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
她吸了吸鼻子,声音带着刻意的顺从:“儿子说得对,老周,咱们……咱们走得体面点。”
周振国看着我们“顺从”的样子,忽然嚎啕大哭起来。
他踉跄着扑过来,一把抱住我和苏慧,鼻涕眼泪蹭了我们一身。
“好,好!我的好老婆,我的好儿子!下辈子,下辈子我一定好好对你们!”
他的怀抱带着令人作呕的酒臭,我和母亲的身体都很僵硬。
黑暗中,我和苏慧交换了一个眼神,那里没有眼泪,只有冰冷的决意。
他很快就醉倒在了沙发上,鼾声如雷。
我和母亲轻手轻脚地收拾了地上的玻璃,把那包老鼠药冲进了下水道。
“小轩,你……”苏慧的声音在发抖。
“妈。”我打断她,握住她冰凉的手,“我们不能死。该死的人不是我们。”
我的手心也很凉,但语气必须坚定。
苏慧看着我,像是第一次真正看清自己十八岁的儿子,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
02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按照“约定”,我们该去水库了。
周振国醒来后,情绪反而平静了些,甚至带着一种殉道般的悲壮。
他翻出了几年前买的、几乎没穿过的亲子装,坚持要我们换上。
“最后一段路,咱们一家人,要齐齐整整的。”
那鲜艳的红色T恤穿在身上,像某种荒诞的祭服。
出门时,邻居老孙正好在遛狗。
“哟,老周,穿这么精神,带老婆孩子去哪儿玩啊?”老孙笑着打招呼。
我抢在周振国前面,露出一个尽可能自然的笑容:“孙叔,我们去城西新开的民俗街逛逛。”
周振国配合地点点头,甚至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手掌粗糙而沉重。
我们坐上了开往城郊的公交车。
越靠近水库,周振国的话就越少,只是紧紧抓着我和母亲的手,抓得很用力。
合金水库在郊区,平时人就少,年节里更是空旷。
冬天的风刮过水面,带着刺骨的寒意。
我们站在水泥砌成的堤岸上,下面墨绿色的河水缓慢而深不可测地流淌着。
周振国望着河水,喉咙里发出哽咽的声音。
“阿慧,我……我对不起你。”他转向母亲,眼泪流了下来,“这些年,你跟着我,没享过福。”
苏慧低着头,肩膀微微耸动,不知是冷的,还是在演戏。
“小轩。”他又看着我,“爸爸没用,没给你一个好条件……下辈子,下辈子我当牛做马补偿你。”
我看着他涕泪横流的脸,心里一片麻木。
他说着,忽然用力抱住苏慧,吻了上去。
那更像是一种发泄和告别,毫无温情可言。
然后,他松开母亲,牵起我的手,又握住母亲的手。
“走吧,不怕,一会儿就不冷了。”他的声音嘶哑,带着一种诡异的温柔。
我们走下有些湿滑的水泥台阶,冰冷的河水渐渐漫过脚踝、小腿。
水很凉,刺得骨头疼。
周振国走在最前面,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像是给自己鼓劲。
当水没过他大腿根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们一眼,眼神复杂。
“阿慧,小轩,别怪我……一家人,就得共进退。”
就在这一瞬间。
我和母亲对视一眼,早已蓄势的力道同时爆发。
我用力将他往前一推,母亲则侧身狠狠撞向他的肋下。
周振国完全没有防备,惊愕的表情定格在脸上,整个人失去平衡,扑通一声栽进深水区。
“你们……!”
冰冷的水花溅起。
他挣扎着冒出个头,手臂胡乱拍打,眼睛瞪得极大,充满了难以置信和愤怒。
他想喊什么,却被灌了一口水,只剩下含糊的咕噜声。
水库准时开闸的轰鸣声从下游隐隐传来,水流肉眼可见地变急了。
周振国像一段枯木,被那股暗涌的力量拽着,迅速向下游卷去,只剩下几个翻滚的水泡。
我和母亲站在齐膝深的水里,一动不动,看着那个身影消失在昏沉的水色中。
没有欢呼,没有大笑,只有冰冷的河水,和更加冰冷的沉默。
我们艰难地爬上岸,浑身湿透,冷得牙齿打颤。
母亲瘫坐在冰冷的堤岸上,嘴唇发紫,眼神空洞。
我脱下湿透的外套,拧了拧水,披在她肩上。
“妈,我们得走了。不能在这里待太久。”
她像是没听见,依旧呆呆地望着水面。
我用力把她拉起来,搀扶着她,一步一步,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身后,是寂静的水库,和一条消失的生命。
03
我们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一家偏僻的小旅馆,用我之前用零花钱办的、周振国不知道的一张身份证开了间房。
热水冲刷着身体,却怎么也驱不散那股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寒意。
我和母亲穿着旅馆提供的廉价睡衣,坐在各自床上,相对无言。
第二天中午,我才用公共电话报了警。
我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惊慌和哭腔:“喂,警察吗?我爸爸……我爸爸昨天说去水库散心,现在还没回来……”
接下来的几天,是按部就班的流程。
配合调查,辨认尸体——那已经肿胀得几乎认不出的躯体。
在派出所,我表现出了一个刚刚失去父亲、强忍悲痛的儿子的所有特征:眼神呆滞,回答问题时偶尔的哽咽,以及努力维持的镇定。
母亲则大部分时间在默默流泪,她不需要太多表演,那份真实的疲惫和恐惧就是最好的伪装。
周振国被定性为“酒后失足落水意外身亡”。
没人怀疑。
死亡证明,户口注销,火化。
一切快得不可思议。
我们去殡仪馆领骨灰盒的时候,工作人员是个面容和善的大姐,她同情地看着我们:“节哀顺变,以后母子俩要互相扶持,好好过日子。”
我们低头道谢,接过那个沉甸甸的黑色盒子。
没有葬礼,没有仪式。
我用快递把骨灰盒寄回了周振国老家的村委会,付了到付。
处理完这些,我和母亲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又去了一家保险公司。
半年前,我说服母亲,用家里最后一点积蓄,为周振国购买了一份高额人身意外险。
受益人是我和苏慧。
如今,这笔钱顺利到账了。
数字不小,足够还清大部分债务,还能让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必为生计发愁。
坐在银行贵宾室里,母亲握着那张新办的银行卡,手一直在抖。
“小轩……我们……”她的话没说完,眼神里交织着解脱、后怕,以及深深的迷茫。
“妈。”我握住她的手,银行卡的边缘硌着掌心,“我们活下来了。这只是开始。”
是的,这只是开始。
周振国死了,但他留下的烂摊子,远没有结束。
04
父亲死后第三天,我们在整理他寥寥无几的遗物时,在他旧西装内侧的口袋里,摸到了一个硬物。
是一枚款式简单的银色戒指,内侧刻着两个字母:Z & W。
周振国和苏慧名字的缩写都对不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
苏慧看到那枚戒指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盯着那两个字母,嘴唇翕动,却没发出声音。
“妈,你认识这个‘W’?”我试探着问。
她猛地摇头,把戒指扔回桌上,像是碰到了什么脏东西:“不……不认识。谁知道他在外面招惹了什么人!”
但她的反应出卖了她。
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默默收起了戒指。
真正的麻烦,在几天后上门了。
周振国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从乡下赶来了。
他们没去我们原来的家——那房子早已抵债——而是不知怎么打听到了我们临时租住的小区。
两个老人就守在小区门口,一看到我和母亲,就像看到了仇人。
奶奶周王氏干瘦的身体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尖利的手指几乎要戳到苏慧脸上。
“苏慧!你个扫把星!把我儿子克死了!你还我儿子命来!”
爷爷周铁柱站在后面,脸色铁青,喘着粗气,浑浊的眼睛死死瞪着我们,满是恨意。
周围很快聚拢了几个看热闹的人。
苏慧被这突如其来的指控气得浑身发抖:“妈!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振国他是自己不小心……”
“放屁!”周王氏唾沫横飞,“我儿子水性好得很!怎么会掉水里?肯定是你!还有你这个小白眼狼!”她转向我,眼神恶毒,“你们合伙害死了他!怕我们见最后一面,急急忙忙就烧了,你们心里有鬼!”
爷爷也跟着吼道:“就是!不然为啥不敢让我们见一面?为啥这么快就烧了?”
他们的逻辑简单而蛮横,却极具煽动性。
围观者的目光开始变得探究和怀疑。
我往前走了一步,挡在母亲身前。
冬天的阳光很淡,照在身上没什么温度。
我看着眼前这两位血脉相连的老人,心里没有任何温情,只有一片冰冷的厌烦。
从小到大,他们没抱过我,没给过我好脸色,只因为我是个“迟早别人家”的孙子。
他们对母亲的苛责和轻视,更是从未掩饰。
“爷爷奶奶。”我的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压过了周王氏的哭嚎,“爸爸去世,我和妈妈比谁都难过。警方已经有结论了,是意外。火化是殡仪馆的正常流程,我们想着快过年了,不想惊动太多亲戚,让爸爸安静地走,这也有错吗?”
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围观的人。
“你们一来,不问青红皂白,就骂我妈是扫把星,说我们害人。这是亲爷爷奶奶该说的话吗?你们有证据吗?”
周铁柱被我问得一噎,周王氏却跳得更凶:“要什么证据?你们娘俩就是证据!我儿子没了,你们倒好,还有钱租房子?钱哪来的?是不是我儿子的保险金?你们早就计划好的!”
她这话歪打正着,却更显胡搅蛮缠。
我懒得再纠缠,直接拿出了手机:“既然你们非要这么说,那我们就请警察来评评理吧。诽谤也是犯法的。”
听到“警察”二字,周王氏的气焰终于弱了一些,但嘴上还不服软:“叫啊!你叫啊!让大家都看看你这不孝子孙怎么对待爷爷奶奶的!”
我真的拨通了110。
警察来得很快。
了解情况后,警察严肃地批评了周家二老:“老人家,失去儿子心情可以理解,但不能胡乱猜测,诬陷他人。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能乱说,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在警察的调解和见证下,周铁柱和周王氏不情不愿地向我们道了歉,保证不再来骚扰。
他们离开时,周王氏回过头,那双浑浊的老眼里闪着怨毒的光,低声嘀咕了一句:“你们等着……有人会收拾你们……”
那句话很轻,却像一根冰锥,刺进了我的耳膜。
有人?
除了他们,还有谁?
那个戒指上的“W”,忽然清晰地浮现在脑海。
05
生活似乎暂时恢复了平静。
我们用保险金还清了最紧急的几笔债务,租了个更安全、也更隐蔽的一居室。
母亲找了份超市收银的工作,工资不高,但能让她有点事做,不再整天胡思乱想。
我则回到了学校,准备高考。
但我知道,平静只是表面。
周王氏那句“有人会收拾你们”,还有那枚刻着“Z & W”的戒指,像两根刺,扎在心里。
我开始有意识地回顾周振国出事前那段日子。
他回家越来越晚,身上有时会有陌生的香水味,不是母亲用的那种廉价花露水,而是一种更馥郁、更成熟的气息。
他接到某些电话时会躲去阳台,声音压得很低。
有一次,我甚至在他的手机充电线插头上,发现了一根棕红色的、长长的卷发。苏慧是黑色的直发。
我把这些零碎的细节拼凑起来,答案呼之欲出。
周振国不仅破产,不仅想拖我们一起死,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女人。
而这个女人,可能知道些什么,甚至可能……与他的“意外”有关联?
这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
我试图从周振国留下的旧物中寻找更多线索,但除了那枚戒指,几乎一无所获。他好像刻意抹去了那个“W”存在的大部分痕迹。
直到一个周末,我在整理他从办公室带回来的、装废品的纸箱时,在一本破旧的工程手册夹层里,摸到了一张硬硬的卡片。
是一张孕检报告单的复印件。
患者姓名一栏被小心地撕掉了,但检查日期清晰可见:去年十一月。
孕周推算,如果孩子保住了,现在应该已经出生了。
报告单右下角,有一个蓝色的、模糊的医院印章,隐约能看出是“市妇幼”几个字。
而在报告单背面,用铅笔写着一串数字,像是一个电话号码,后面跟着一个潦草的字:“薇”。
薇。W。
心脏在胸腔里重重地跳了一下。
周振国不仅出轨,对方还怀孕了。
时间点,正好在他生意急转直下、开始频繁酗酒之前。
一个荒诞而冰冷的念头浮现:他的破产,会不会也和这个女人有关?
我拿着这张单子,去找母亲。
苏慧看到孕检单的瞬间,整个人晃了一下,扶住了桌子边缘。
她的脸上没有太多惊讶,只有一种深切的疲惫和果然如此的惨淡。
“果然……是她。”她喃喃道。
“妈,你认识?这个‘薇’是谁?”我追问。
苏慧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窗外天色渐暗,屋里没开灯,她的脸沉浸在阴影里。
“吴雪薇。”她终于开口,声音干涩,“你爸……很多年前就认识她。后来断了联系。我以为……我以为早就结束了。”
很多年前?那岂不是在和我母亲结婚之前?
“他们一直有联系?”我问。
苏慧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神情混乱:“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爸出事前几个月,我好像在商场远远见过一个背影,很像她,当时还以为看错了……”
现在看来,并没有看错。
“这个孩子……”我看着孕检单。
“如果生下来了,现在应该刚满月不久。”苏慧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空洞的讽刺,“你爸一直想要个女儿。他常说,女儿贴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周振国后期对我和母亲如此冷漠甚至残忍?
因为外面有了更符合他“期待”的新家庭?
因为他觉得我们是累赘,阻碍了他奔向新生活?
甚至他最后想拉着我们一起死,除了绝望,是不是也有那么一丝……为那个“薇”和未出生的孩子扫清障碍的狠毒?
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
如果真是这样,那个吴雪薇,对我们母子,知道多少?又参与了多少?
周振国的“意外”,她是否知情?周王氏那句“有人会收拾你们”,指的会不会就是她?
问题一个接一个,却没有答案。
我收起孕检单,对苏慧说:“妈,这件事交给我。你安心上班,别想太多。”
苏慧担忧地看着我:“小轩,你别乱来。我们好不容易才……”
“我知道。”我打断她,“我不会乱来。但我们必须知道,潜在的危险是什么。”
敌在暗,我在明。
这种感觉糟糕透了。
06
我尝试用那张孕检单背面的电话号码,去搜索社交账号。
一无所获。那可能是个不记名的临时号码。
“吴雪薇”这个名字太普通,在本地人口信息里能搜出几十个,年龄符合的也有好几个,无法锁定。
线索似乎断了。
但我没放弃。
周振国生前最后一段时间,精神状态很差,如果他和吴雪薇频繁联系,或许会留下一些电子信息之外的痕迹。
我又仔细搜查了我们曾经的家——那套即将被法院拍卖的旧房。
在书房写字台最底下的抽屉背面,用胶带粘着一个薄薄的、塑料密封袋。
里面是一张很小的、看起来像随手写的便签纸。
上面只有一行字,是周振国的笔迹,写得有些凌乱:“老地方,三月十五,晚九点,彻底解决。薇。”
三月十五,就是他出事的前一周。
老地方?彻底解决?
解决什么?怎么解决?
这张便签纸,像一块投入死水的石头,让我浑身的血液都冷了下来。
它印证了我最坏的猜测。
周振国和吴雪薇,不仅保持着联系,而且在计划着什么。
而这个计划的对象,极有可能就是我和母亲。
“彻底解决”,这四个字充满了冰冷的决绝。
周振国在出事前,是否已经着手实施这个计划?只是被我们抢先了一步?
或者,这个计划本身,就包括了他自己的“脱身”与我们的“消失”?
吴雪薇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帮凶?策划者?还是知情者?
她现在在哪里?那个孩子又在哪里?
她知道周振国已经“意外”死亡了吗?
如果知道了,她会有什么反应?
是偃旗息鼓,还是……
周王氏那句充满恨意的“有人会收拾你们”,再次回响在耳边。
我捏着那张小小的便签纸,站在布满灰尘的旧屋里,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黑暗并未随着周振国的消失而散去。
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潜伏在看不见的地方,也许正在窥伺着我们。
07
三月十五早已过去,那个“老地方”的约定自然失效。
但我需要知道,“老地方”是哪里。
周振国的手机通讯记录里没有线索,社交软件记录也被清理得很干净。
我尝试从消费记录入手。
翻查他出事前几个月的信用卡账单、电子支付记录,寻找是否有规律性的、指向特定场所的消费。
终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在去年九月到十一月期间,也就是孕检单时间前后,周振国有多次在“静谧茶舍”的消费记录,金额不高,都是两百左右,时间多是工作日的下午或晚上。
这家茶舍我知道,在城东一个不算热闹但环境清幽的文创园区里,离周振国原来的公司很远,也不靠近我们家。
他一个人,或者普通的商务会面,去那里的可能性不大。
而且,十一月之后,这类消费记录就中断了。
是因为吴雪薇怀孕显怀了不方便外出?还是因为他们换了更隐蔽的联络地点?
“静谧茶舍”会不会就是所谓的“老地方”?
无论如何,这是我目前唯一的、具体的线索。
我决定去一趟。
选了一个周六的下午,我独自坐公交车来到了文创园区。
“静谧茶舍”的门面不大,原木色装修,挂着竹帘,看起来确实很安静。
我推开沉重的木门,风铃发出清脆的响声。
店里人不多,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檀香和茶香。
一个穿着素色茶服的女服务员迎上来,微笑询问:“先生一位吗?”
我点点头,目光快速扫过店内。
布局是常见的茶舍风格,有半开放的卡座,也有用竹帘或屏风隔开的私密小包间。
“请问……有没有一位姓周的先生,或者一位姓吴的女士,在这里寄存过东西,或者有没有固定的预留位置?”我试探着问,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只是个帮忙跑腿的。
服务员露出抱歉的笑容:“不好意思,先生,我们不方便透露客人信息的。而且,我们这里没有寄存服务,也不接受长期预留位置。”
意料之中的回答。
我点了最便宜的一壶茶,在一个靠窗的角落坐下。
我需要观察。
茶香氤氲,我小口啜饮着,注意力却放在进出的客人,以及店内的服务员身上。
或许,吴雪薇是这里的常客,服务员会认得她?
坐了近两个小时,毫无收获。
来的大多是情侣、朋友,或者谈事的商务人士,没有独身的、符合我想象中“吴雪薇”形象的女人。
天色渐晚,我准备离开。
结账时,我还是不死心,换了个方式问:“姐姐,我其实是帮我叔叔来找人的。他之前常来这里和一个朋友喝茶,最近他……出了点事,联系不上那位朋友了。他朋友可能是个长卷发,挺有气质的女士,大概三十多岁。您有印象吗?”
服务员一边操作收银机,一边想了想,还是摇头:“抱歉,每天客人不少,我没什么特别的印象。”
看来这条路也行不通。
我有些失望地走出茶舍。
初春的傍晚,风还是有些凉。
我拉紧了外套,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难道真的只能被动等待,等那个“薇”或者周家二老再次找上门来?
就在我低头走过茶舍侧面一条窄窄的、堆放着一些清洁工具和废弃纸箱的后巷时,脚下忽然踢到了什么东西。
是一个硬硬的、反光的小物件,滚到了墙角。
我弯腰捡起来。
是一个耳钉。
很简单的款式,一颗小小的、水滴形状的黑色锆石,镶嵌在银色的底座上。
这种耳钉很常见。
但引起我注意的是,耳钉的背面,银色的扣针内侧,似乎刻着极小的字母。
我眯起眼睛,凑到巷口稍亮一点的光线下仔细辨认。
那是两个花体英文字母,刻得很浅,但能看出来:W.X。
W.X. 吴雪薇?
心脏猛地一跳。
这是巧合吗?
还是……这就是吴雪薇的东西?她在这里遗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