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拆迁我拿600万第一个搬走。
村里剩下的14户钉子户围着我的空屋,笑我眼皮子浅,骂我是叛徒。
他们团结一心,誓要每户多熬出80万。
几个月后,一则新的区域规划调整方案悄然公示。
他们守着化工厂哭了。
01
村口告示栏贴上红纸头文件的时候,整个田家坳都炸开了锅。
田文远是第一个晓得的。
他当时正端着碗,蹲在自家老屋的门槛上,扒拉着最后一口咸菜炒饭。
村主任孙有福背着手晃过来,用脚尖碰了碰田文远屁股底下的门槛石。“还吃呢?”孙有福的声音里压着一股子藏不住的欢喜,像是过年揣了压岁钱的小孩。“好事,天大的好事来了。”
田文远抬起头,饭粒还粘在嘴角。
孙有福把手里卷着的几张纸抖开,哗啦一声,贴在了田文远家斑斑驳驳掉着墙灰的外墙上。
白纸黑字,红彤彤的公章。
最顶上那行加粗的字体,像烧红的烙铁,烫进田文远的眼睛里。
《田家坳片区整体拆迁改造通知》。
田文远的筷子掉在了地上。
碗底还剩着一口饭。
“咱们村,要拆了。”孙有福点了根烟,眯着眼,吐出的烟雾在午后的阳光里慢悠悠地飘。“评估公司过两天就来,挨家挨户量房子,算价钱。你家的位置,加上这老屋的面积……”他用夹烟的手指,点了点田文远身后的三间瓦房。“估摸着,少不了。”
田文远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他慢慢站起身,腿有点发麻,趔趄了一下才站稳。
墙上的通知,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补偿标准,安置方案,时间节点。
看到最后那个评估补偿金额的预估范围时,田文远的呼吸停了几秒。
数字后面跟着的一长串零,晃得他眼晕。
“文远啊。”孙有福拍了拍他的肩膀,力气有点大。“你是村里年轻人里,念过书的,明白事理。带个好头。”
这句话,听起来轻飘飘的。
落在田文远耳朵里,却沉甸甸的。
他没吭声,只是盯着那张通知。
孙有福走了,哼着不成调的小曲。
田文远还站在原地。
傍晚的风吹过来,墙上的通知哗哗作响。
远处,已经有村民围到了村口的告示栏前。
嗡嗡的议论声,像夏天的蚊群,顺着风飘过来。
“拆了?真拆了?”“能给多少?”“我看隔壁大王庄拆迁,一家赔了四百来万呢!”“咱们这位置偏,能跟人家比?”“那可说不准……”
声音里掺杂着怀疑,兴奋,盘算,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张。
田文远弯腰,捡起地上的筷子和碗。
转身进了屋。
屋里很暗,老式的木格窗户透不进多少光亮。
空气里有灰尘和潮气混合的味道。
这是爷爷留下的房子。
父亲走得早,母亲改了嫁,田文远是跟着爷爷在这三间瓦房里长大的。
前年爷爷也走了。
现在就剩他一个人。
他把碗筷搁在灶台上,没洗。
走到里屋,从床头柜抽屉最里头,摸出一个铁皮盒子。
打开。
里面是爷爷的身份证,户口本,几张泛黄的老相片。
还有一本存折。
存折上的数字,很小。
是田文远在省城打工三年,一点点攒下来的。
原本的打算,是再过两年,攒个首付,在省城边上买个小点的公寓。
把爷爷接过去。
现在爷爷不在了。
这老屋,也要没了。
田文远坐了许久,直到天色完全黑透。
隔天一早,评估公司的人就来了。
开着辆白色面包车,拿着激光测距仪,照相机,还有厚厚的表格。
领头的姓赵,戴着眼镜,看起来很干练。
说话客气,但没什么温度。
“田先生是吧?我们来测量一下您家的房屋面积和结构。麻烦配合一下。”
田文远点了点头,让开身子。
两个工作人员拿着仪器进了屋,嘴里啪啦地拍照,测量,记录。
赵组长站在院子里,打量着这栋老屋。
“砖木结构,瓦顶,年代比较久了。墙体有裂缝,屋顶有些漏雨痕迹。宅基地面积倒是不小,连带院子,有差不多两百平。”
他一边说,旁边就有人在本子上飞快地记。
田文远安静地听着,像是在听别人的事情。
测量进行了大概一个钟头。
赵组长拿着初步的评估单,走到田文远面前。
“田先生,根据目前的测算和补偿标准,您这处房产的初步评估价,在六百万元左右。”
六百万元。
田文远的指尖,微微颤了一下。
“这只是初步评估,最终以正式评估报告和拆迁补偿协议为准。”赵组长推了推眼镜。“具体的补偿方案,有两种。一是货币补偿,就是直接拿钱。二是产权置换,可以置换到规划中的安置房小区,按照面积折算。您考虑一下。”
赵组长留下了一张联系名片,和一叠宣传资料。
然后带着人,去了隔壁。
田文远拿着那张评估单,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
阳光很刺眼。
六百万元。
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在省城打工,一个月累死累活,除掉房租吃饭,能剩下四千块,就算不错。
六百万元。
他要干一百二十五年。
还得不吃不喝。
下午,村里就传遍了。
“田家那小子,评估了六百万!”“我的天,这么多?”“他家那破房子,值这么多?”“宅基地大啊,连着院子呢。”“啧啧,真是走了运。”
议论声中,有羡慕,有嫉妒,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田文远没出门。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手机调了静音。
但消息还是不断涌进来。
先是二伯田建军的电话。
打了三遍,田文远才接起来。
“文远啊,评估完了?多少?”
二伯的声音,有点急切,又努力装得随意。
田文远沉默了两秒。
“六百万左右。”
电话那头,呼吸明显重了一下。
“哦……六百万,不少,不少。”二伯干笑了两声。“那你打算怎么办?签字拿钱?”
“嗯。”
“这么急?”二伯的语气变了变,“不再看看?跟其他家商量商量?咱们要是团结起来,说不定能要得更多!”
田文远没说话。
“文远,你听二伯说,拆迁这事,谁先签字谁吃亏。你得沉住气,跟大家一起,当钉子户。开发商急着要地,拖得越久,他们给的钱就越多。隔壁村就有例子,最后多要了一百多万呢!”
二伯说得唾沫横飞,好像那多出来的一百万已经揣进了口袋。
田文远听着,眼睛看着屋顶黑黢黢的房梁。
“二伯,我知道了。我再想想。”
他挂了电话。
02
没过半个钟头,三婶刘淑珍直接上门了。
手里拎着一袋刚摘的黄瓜,笑吟吟的。
“文远,吃饭了没?三婶给你送点菜。”
她把黄瓜放在灶台上,眼睛却四处打量。
“听说评估完了?六百万?”
田文远点了点头。
刘淑珍一拍大腿。
“好事啊!你爷爷在天之灵,也该放心了。”
她在板凳上坐下,叹了口气。
“就是这钱啊,听着多,真拿到手,不经花。你看现在省城的房价,好点的地段,一平都得三四万。六百万,也就买个一百多平的房子,装修一下,剩不下多少了。”
她话锋一转。
“要我说,你先别急着签字。咱们村十四户人家,要是拧成一股绳,一起跟拆迁办谈条件。每户多要个几十万,那不是轻轻松松?你年轻,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听三婶的,准没错。”
田文远给三婶倒了杯水。
“三婶,拆迁办给的补偿标准,是按政策来的吧?”
刘淑珍一愣,随即摆摆手。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这么多户人家,他们敢强拆?拖下去,急的是他们。”
正说着,外面传来嘈杂的声音。
田文远走到门口,看到七八个村民,正簇拥着一个人,朝这边走来。
被簇拥在中间的,是徐满囤。
村里辈分高,脾气倔,儿子在城里据说有点关系。
此刻他背着手,昂着头,像个得胜的将军。
一群人,停在了田文远家院门外。
“文远在家呢?”徐满囤嗓门洪亮。
田文远走出来。
“徐伯。”
徐满囤上下打量了他一遍。
“评估了六百万?”
“嗯。”
“打算签字了?”
田文远没回答。
徐满囤哼了一声。
“年轻人,眼皮子浅。六百万就把你打发了?”
他转过身,对着跟来的村民,也像是对着田文远说。
“咱们田家坳,十四户人家,今天就把话撂这儿。补偿标准,每户至少再加八十万。不给?我们就钉死在这儿,看他们怎么拆!”
人群里响起附和声。
“对!加八十万!”“团结起来!”“不能便宜了他们!”
群情激愤。
田文远站在门口,像是个局外人。
徐满囤的目光,又落回他身上。
“文远,你爷爷在的时候,也是个硬气的人。别到了你这辈,软骨头的名声传出去。”
这话,有点重了。
旁边的村民,眼神都看了过来。
田文远的手,在身侧慢慢握紧。
又松开。
“徐伯,我再想想。”
徐满囤似乎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但也没再说什么。
挥了挥手,带着人又往下一家去了。
嘈杂声渐渐远去。
田文远回到屋里,三婶刘淑珍还没走。
“看见没?”刘淑珍压低声音。“徐满囤带头了。大家都跟着他。你这时候签字,就是跟大家作对,懂吗?”
田文远看着三婶。
“作对会怎么样?”
刘淑珍被问住了,张了张嘴。
“也不会怎么样……就是,名声不好听。以后在村里,抬不起头。亲戚之间,也难相处。”她顿了顿,又补充道。“再说了,你一个人先拿了钱,搬走了。我们要是后面真多要到了钱,你心里不后悔?”
田文远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鞋面上沾着泥。
“三婶,我有点累,想歇会儿。”
刘淑珍看了他两眼,终于站起身。
“行,你好好想想。三婶不会害你。”
她走了。
屋里终于彻底安静下来。
田文远坐到爷爷生前常坐的那把旧藤椅上。
椅子发出吱呀的声响。
他拿出手机,打开计算器。
六百万元。
减去在省城买套普通两居室的钱,减去简单装修的钱,减去……
算到最后,还能剩下不少。
可以存起来。
可以做点小生意。
可以……喘口气。
不用再每天加班到深夜,不用再看老板脸色,不用再担心下个月的房租。
爷爷治病欠下的那点债,可以轻松还清。
甚至,可以给爷爷修个像样点的墓地。
他闭上眼睛。
眼前晃动的,是爷爷临终前枯瘦的手,握着他,说不出话。
是省城出租屋里,永远潮湿的墙壁。
是老板把文件摔在他桌上时,飞溅的唾沫。
是银行卡余额,永远停留在四位数。
田文远睁开眼。
拿起赵组长留下的那张名片。
按照上面的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很快接通。
“喂,赵组长吗?我是田文远。对,田家坳的。我考虑好了。我选择货币补偿。签字……越快越好。”
电话那头,赵组长似乎也有些意外。
沉默了两秒。
“田先生,您确定吗?不需要再和家人,或者村里其他人商量一下?”
“不用。”
田文远的声音,很平静。
“我自己的房子,自己决定。”
“好。”赵组长的语气里,多了一丝公事公办的干脆。“那明天上午九点,您来拆迁办临时办公室。我们签订正式的补偿协议。协议签订后,补偿款会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打到您指定的账户。”
“谢谢。”
田文远挂了电话。
放下手机的那一刻,他的手心全是汗。
隔天,田文远起了个大早。
换了一身相对干净的衣服。
出门前,他在爷爷的遗像前站了一会儿。
照片里的爷爷,严肃地看着他。
“爷爷,我走了。”
他轻声说。
然后转身,锁上了老屋的门。
拆迁办临时办公室,设在村委原来的会议室里。
田文远到的时候,门口已经围了一些人。
都是听到风声来看热闹的村民。
看到他,交头接耳的声音更响了。
“真来了?”“还真要第一个签字?”“啧啧,六百万就把他收买了。”“年轻人,没经过事。”
田文远目不斜视,走了进去。
赵组长已经在里面等着,桌子上摆着厚厚一沓文件。
“田先生,请坐。这些是补偿协议,条款您仔细看一下。主要是补偿金额,支付方式,搬离期限,以及您的权利和义务。”
田文远坐下来,一页一页地翻看。
协议很规范,补偿金额写着陆佰万元整。
支付方式是银行转账。
搬离期限是协议生效后三十天内。
他看得很慢。
门外,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忍不住喊了一嗓子。
“文远!别犯傻!再等等!”“就是!现在签了,以后别后悔!”
声音透过门缝传进来。
赵组长皱了皱眉,看了一眼田文远。
田文远好像没听见。
他拿起笔。
笔尖悬在签字栏上方。
停了大概有五秒钟。
然后,落下。
田文远。
三个字,写得有点用力,力透纸背。
赵组长松了口气,脸上露出职业化的笑容。
“田先生,恭喜。后续款项支付和搬离事宜,我们会专人跟您对接。”
田文远收起自己那份协议,站起身。
“谢谢。”
他走出办公室。
门外的阳光,白得晃眼。
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
所有的目光,都钉在他身上。
有不解,有鄙夷,有嘲弄,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田文远穿过人群,往外走。
背后,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签了,真签了。”“第一个叛徒。”“六百万就把他魂勾走了。”“等着吧,有他后悔的时候。”
田文远的脚步,没有停。
他径直走回了家。
开始收拾东西。
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
大部分家具都老得不能要了。
他只带走了爷爷的遗像,铁皮盒子,几件常穿的衣服,和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小物件。
一个行李箱,一个编织袋,就装完了他在这个家二十八年的一切。
下午,他打电话叫了辆小货车。
司机把车开到院门口时,又引来一阵围观。
田文远把东西搬上车。
最后看了一眼老屋。
瓦片灰暗,墙壁斑驳。
院子里爷爷种的柿子树,叶子已经掉光了。
他上了副驾驶。
“师傅,走吧。”
货车发动,驶出村子。
后视镜里,老屋越来越小。
村口聚集的人群,也变成了模糊的黑点。
田文远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车子开出田家坳地界的时候,他的手机震了一下。
是二伯田建军发来的微信。
很长一段语音。
点开。
二伯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尖利。
“田文远!你翅膀硬了是吧?!谁让你签字的?!跟你商量了吗?!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二伯?!有没有这些亲戚?!第一个签字搬走,你让村里人怎么看我们田家?!说你是个软骨头!见钱眼开!没出息的东西!我告诉你,你现在回来,跟拆迁办说反悔,还来得及!不然,以后你就别认我这个二伯!”
语音到这里,戛然而止。
田文远听完,脸上没什么表情。
他把手机屏幕按灭。
看向窗外。
路边的田野飞快地向后退去。
远处,城市高楼的轮廓,已经隐约可见。
小货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咂了咂嘴。
“兄弟,家里事儿?”
田文远“嗯”了一声。
“拆迁?”
“嗯。”
“赔了不少吧?”
“还行。”
司机笑了笑,有些羡慕,又有些别的意味。
“第一个签字搬走的?”
“嗯。”
司机不说话了,只是摇了摇头。
那意思,不言而喻。
田文远没解释。
03
他知道,从签下名字的那一刻起,他在田家坳很多人眼里,就已经是个“傻子”了。
一个被六百万就轻易收买,背叛了“集体利益”的傻子。
一个目光短浅,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傻子。
小货车开进省城,停在了田文远提前租好的一个临时单间楼下。
房子很小,只有二十平,但干净,有独立的卫生间。
签了三个月短租。
他把行李搬上去,简单归置了一下。
爷爷的遗像,摆在唯一的小桌子上。
做完这些,天已经黑了。
他下楼,在路边小店吃了一碗牛肉面。
面很烫,雾气氤氲上来,模糊了眼镜片。
他摘下来,擦了擦。
口袋里,拆迁补偿协议硬硬的,硌着腿。
手机又震了。
这次是村里的微信群。
群名很朴素:“田家坳一家亲”。
平时没人说话,只有过年过节发发红包。
现在,消息已经刷到了99+。
田文远点开。
最新的一条,是三婶刘淑珍发的。
没有文字。
只有一张图片。
图片拍的是拆迁办门口,田文远签字出来时的背影。
拍得有点模糊,但能认出是他。
图片下面,跟着一条徐满囤发的语音。
田文远点开。
徐满囤苍老而洪亮的声音,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从听筒里传出来。
“看见没?咱们村的‘急先锋’。第一个投降的。六百万,就把他田家的骨气给卖了。也好,少了这种不齐心的,咱们剩下的十四户,更团结!钉子户,咱们当定了!不拿到满意的加价,绝不搬!让那些急着签字的傻子,后悔去吧!”
语音发完,群里立刻炸出一片响应。
“徐伯说得对!”“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十四户,一条心!”“看谁熬得过谁!”“田文远,你就抱着你的六百万后悔去吧!”“以后化工厂建到你家门口,可别哭!”“哈哈哈……”
嘲讽,奚落,幸灾乐祸。
一条接一条。
田文远默默看着。
手指划到最上面,看到二伯田建军也在群里发话了。
语气痛心疾首。
“我这个侄子,我是管不了了。让他别签,非要签。年轻人,不听老人言。以后吃亏在眼前。我们老田家,没这种见利忘义的人!”
下面是一串安慰和附和。
“建军叔别生气,他不听劝,自己选的路。”“就是,以后有他哭的时候。”“咱们剩下的,心齐就行。”
田文远关掉了群聊。
设置了免打扰。
牛肉面已经有点凉了。
他端起碗,把汤也喝干净。
付钱,走出小店。
城市的夜晚,灯火通明。
车流如织,人声嘈杂。
田文远站在路边,看着这一切。
口袋里的协议,似乎又烫了一下。
他深深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
再缓缓吐出。
转身,走向那栋灯火阑珊的出租楼。
背影很快消失在城市的夜幕里。
而一百多公里外的田家坳。
夜色同样笼罩着那十四户尚未签字的人家。
灯光从窗户透出来。
隐约还能听到一些激动的议论声。
关于团结。
关于加价。
关于如何当好一个“钉子户”。
关于那个率先离开的“傻子”。
夜风吹过村口已经空荡荡的田家老屋。
卷起几片枯叶。
悄无声息。
小货车的尾灯消失在村口土路的拐角。
扬起的那点灰尘,很快也落定了。
田家老屋的门上了锁。
那把旧挂锁,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冷冰冰的光。
院里的柿子树,光秃秃的枝桠指向天空,像一双干枯的手。
村口小卖部门口,人越聚越多。
徐满囤蹲在水泥台阶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
烟锅里的火光,随着他用力吸吮,明明灭灭。
“走了。”他吐出个烟圈,慢悠悠地说。“第一个孬种,走了。”
旁边有人接话,是村里的孙老四,嗓门大。
“走得好!少他一个,咱们还清净!”“就是,六百万就屁颠屁颠跑了,没见过钱似的。”“他家那破房子,六百万,偷着乐吧。”“乐?我看他能乐几天。”
三婶刘淑珍嗑着瓜子,瓜子皮随口吐在地上。
“年轻人,眼皮子浅,不懂事。等咱们熬到每户多赔百八十万,看他肠子悔青不。”
人群嗡嗡地议论着。
话题围绕着田文远,围绕着那六百万,围绕着即将到来的“胜利”。
仿佛田文远的离开,不是一种个人的选择。
而是一种背叛。
一种对“集体”的背叛。
一种可以被肆意嘲笑和评判的愚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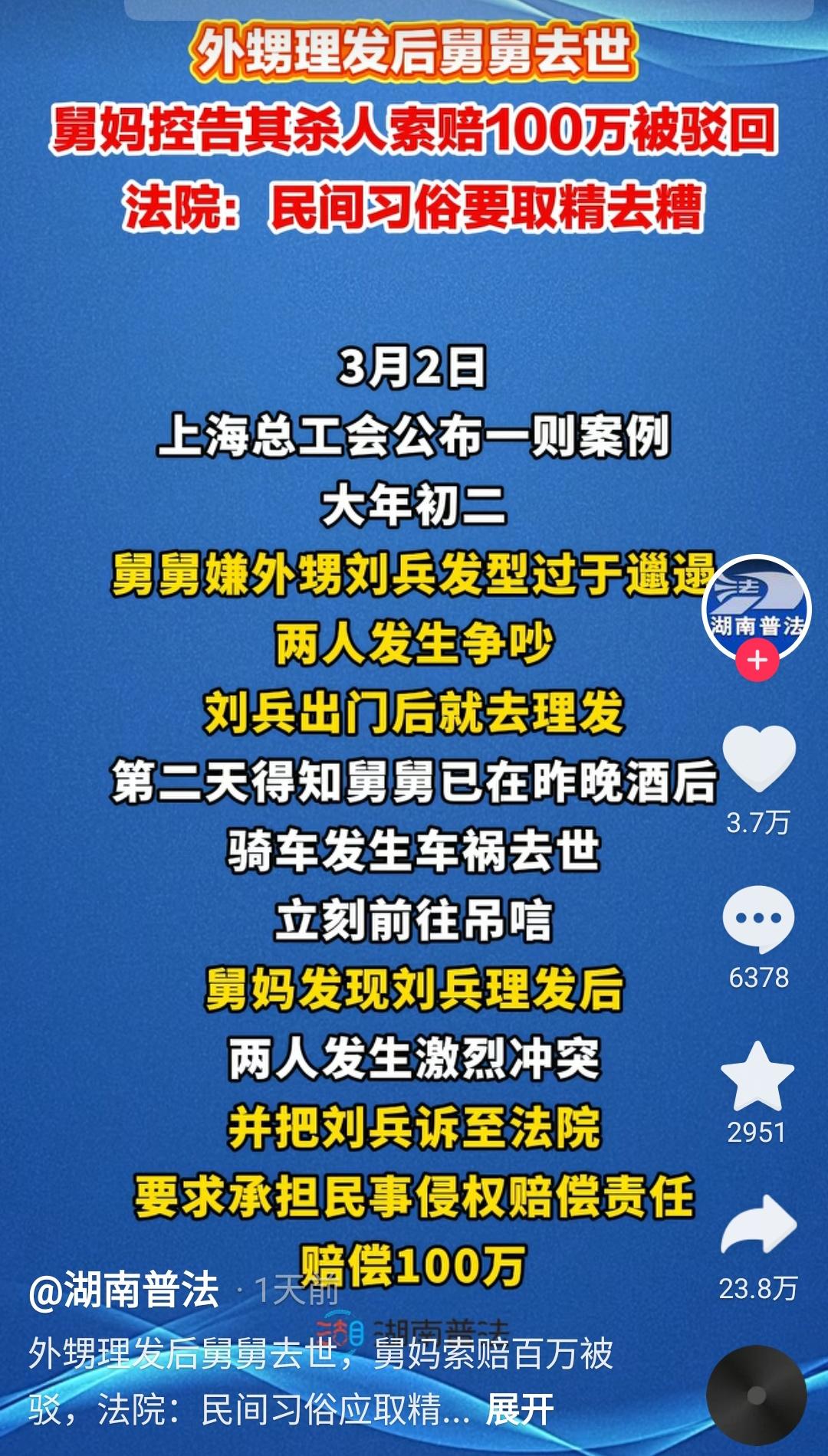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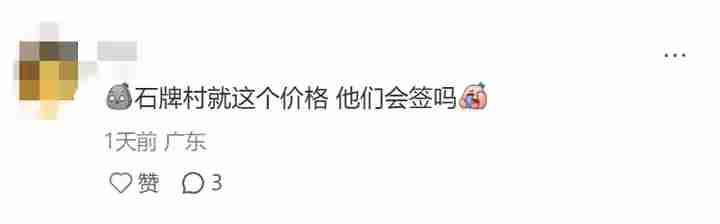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