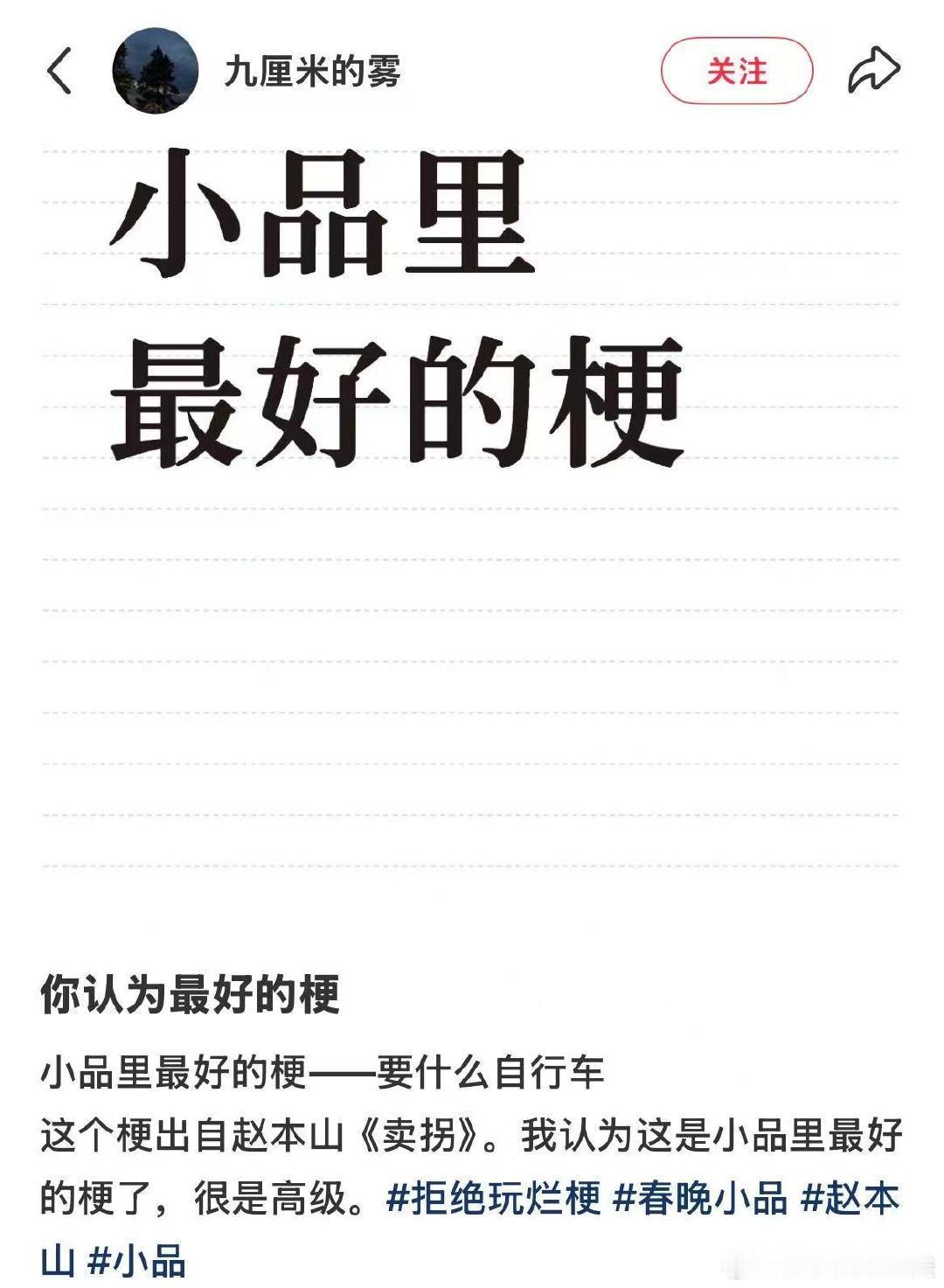“每逢春晚必思赵。”
这句话,已经成为了每一年的保留节目,是全国观众的一种执念,春晚已经进行到了第三次大联排,参演明星也基本被路透了个遍。

小品演员阵容大换血,也让不少观众心捏了一把汗,可奇怪的是,话题中被反复提及的,偏偏是哪个没到场的人。
这位已经退出春晚舞台十几年的“小品之王”,就像江湖里的传说,人不在江湖,但江湖处处都是他的传说。
2026年春晚第三次联排结束后,一份演员名单在业内流传开来,引发的讨论远不止“谁上谁下”这么简单。

从名单本身来看,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节目调整,而更像是一场已经持续十多年的喜剧路线选择,在这一年被集中呈现出来。
最直观的变化,是中生代喜剧演员的整体退场,那个曾在过去几年试图扛起大旗的“中生代”阵营,贾冰、潘斌龙等过去几年被视为“接班人”的名字,在此次联排中集体缺席。
取而代之的,是以李雪琴、徐志胜为代表的脱口秀体系,以及艾伦、常远等更偏向“喜剧综艺化”的演员组合,脱口秀演员和“喜人”正在成建制地接管舞台。

这种变化,并不只是审美轮换,而是喜剧表达方式的结构性转移,从依赖生活经验与情境铺陈,转向以高密度语言梗、标签化人设和即时反馈为主。
老一代演员并非完全消失,64岁的蔡明第28次站上春晚舞台,尝试以“腹语”等形式突破原有表演路径,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即便是经验最丰富的老将,也必须主动适应碎片化、快节奏的审美环境,才能获得舞台空间,这并非个人选择,而是整体生态倒逼的结果。
在这样一轮洗牌中,唯一显得相对稳定的,依然是沈腾和马丽,这是他们第10次合作,也是当前春晚舞台上少数仍具备稳定观众预期的组合。

但这种“稳定”,本身也在反向提醒一个现实问题:到了2026年,中国喜剧舞台依然缺乏真正完成代际接力的核心力量。
偌大一个中国喜剧界,怎么到了2026年,还是只能指望这一对搭档来守住最后的底线?
这一切,并非突然发生,早在2012年前后,春晚喜剧就已经站在分岔路口,当年在导演体系中被反复强调的,是“立意优先”“价值表达”。

在这种创作逻辑下,单纯依靠喜剧效果本身已经不够,作品必须承担明确的教化功能。这一变化,直接导致赵本山与春晚制作体系的根本性冲突。
赵本山当年提交的《小偷》《相亲2》,在创作成熟度和观众接受度上都不存在问题,但因为“缺乏教育意义”被否定。
这位来自黑土地的“小品王”,信奉的是另一套最朴素的哲学:快乐第一,老百姓累了一年了,大年三十还要被教育,这合理吗?显然不合理。

这并不是一次技术分歧,而是两种喜剧观的正面碰撞,一种认为春节晚会首先应该让人笑,另一种则坚持喜剧必须服务于明确的主题表达。
很多人后来把赵本山的退出,归结为身体原因,不可否认,彼时他的身体状况确实已经吃紧,2013年的后台,人们见过他吸着氧、打着点滴熬夜改本子的惨状,生理机能确实到了极限。
但真正让他离开的,不是高血压,而是对创作方向失去掌控后的挫败感,是那种“快乐必须成为教育附庸”的无力感,当“快乐”必须依附于“说教”,当笑声需要为升华让路,赵本山选择了不再妥协。

他把话撂在了桌面上:如果为了凑合演一个自己都不信的东西,那不如不演。
从他离开开始,春晚小品的整体走向逐渐固化:前半段制造笑点,后半段强行转向煽情和总结。
这种模式在短期内可以成立,但长期来看,消耗的是喜剧本身的生命力,讽刺被削弱,荒诞被收紧,人物不再来源于真实生活,而更像是为完成主题服务的工具。

到了2026年,这种后果已经非常清晰。舞台上的喜剧内容越来越依赖网络热梗、流行话题和人设标签,创作周期被压缩,生活观察被替代,结构趋于同质化。
观众或许会笑,但很难再出现那种跨年龄、跨地域的集体共鸣,沈腾和马丽依然具备强大的舞台号召力,但必须承认,他们的影响力更多集中在特定观众层,而尚未形成当年赵本山那种“全家通吃”的覆盖能力。
曾经的小品,可以同时让孩子、成年人和老人产生共振,而如今的喜剧,更像是分众内容的集合。

因此,“每逢春晚必思赵”并不是简单的怀旧情绪,而是一种对喜剧功能变化的集体感知。被怀念的,不只是某一个演员,而是那个允许笑声不必承担额外任务的年代。
2026年的春晚,在制作水平、舞台技术、演员配置上都无疑更加成熟,但也更精密、更安全,当所有情绪都需要被计算、被校准、被审核,喜剧所剩下的空间,自然会变得有限。
或许观众最终会适应这种变化,就像适应很多已经无法逆转的现实一样,但问题仍然存在:当笑声不再纯粹,当喜剧被过度功能化,它是否还能承担起在一年终点为大众释放压力的角色,这本身,已经值得反复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