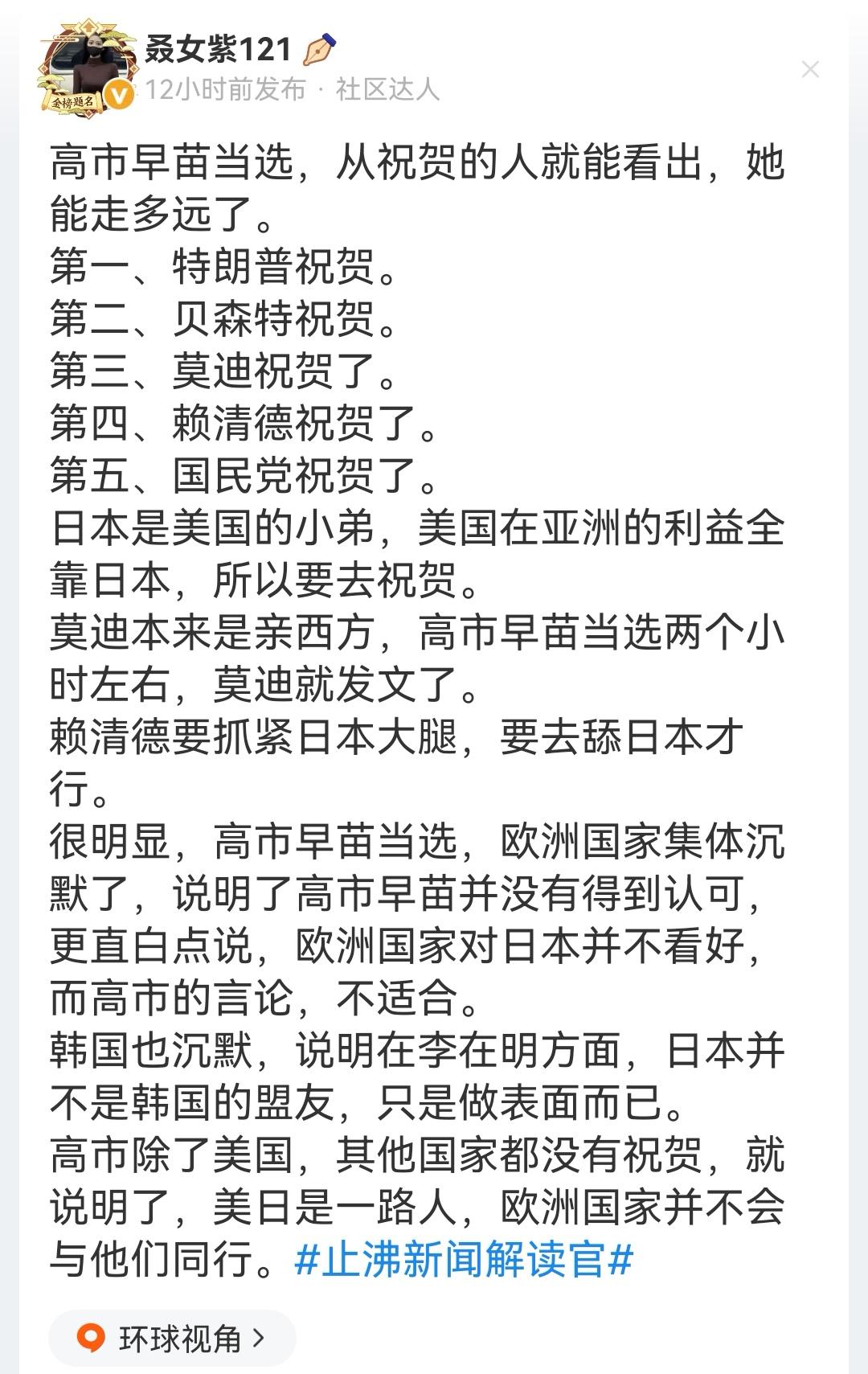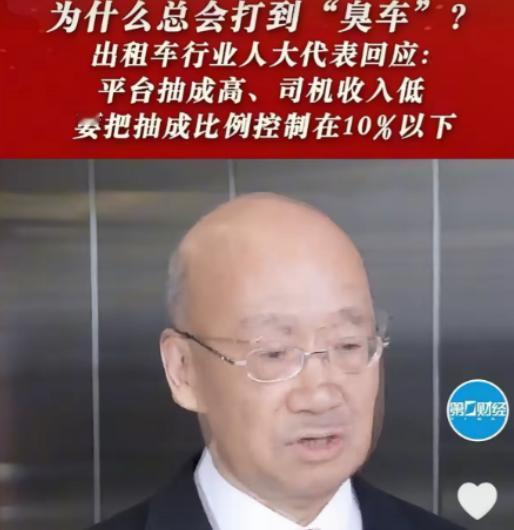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发达国家宁可“自废武功”,也要去工业化? 发达国家把低附加值、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出去,保留设计、品牌、标准和利润最高的部分。这种选择不是退化,而是资本在特定阶段主动追求更高回报的系统安排。市场经济里,生产效率提升往往超过工资增长,导致国内消费跟不上产量,过剩危机周期性爆发。把低端制造放到人力成本低、环保要求松的国家,能让过剩压力和就业矛盾在境外释放,本土只做高端消费市场。 同时,这种转移还能培育新市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后,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收入增加,对欧美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扩大。产业转移因此实现成本降低和市场扩张双重目标。冷战结束后,西方主导全球贸易规则,资本把生产链条组装成全球最低成本体系。企业外包组装环节,本土保留研发和核心部件,大部分利润留在国内。代工方主要获得加工费。 90年代后,这种分工对西方资本是优选方案。他们把产业链分散到多个国家,相互制衡,避免任何一方形成完整体系。西欧、日本、韩国专注精密机床、汽车、半导体等高附加值领域,中东、澳大利亚、俄罗斯提供原料,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后承担大量劳动密集型装配,成为供应链关键节点。 中国加入世贸后,出口从2001年的2660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10年的1.58万亿美元。初期主要从事组装,随后逐步补齐上下游,从原材料、零部件到整机制造,形成完整工业体系。规模效应、基础设施和工程师队伍支撑这种升级。原本设想的分散链条未能有效制约,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市场和强大组织能力的工业体,完成了从低端到中高端的攀升。 信息技术革命与以往工业革命不同。过去大型工厂吸纳大量就业,创造中产阶层;信息技术产业利润高,但核心岗位有限,中型企业往往仅几百人规模。制造业岗位外迁后,信息技术未能提供足够替代就业,大量劳动力转向低端服务业,同时面临移民竞争。欧洲、日本、韩国原本依赖高端制造红利,但在2001年至2019年间,美国科技创新与中国应用落地结合,形成互补效应,欧盟等地区相对滞后。 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业结构问题凸显,制造业回归呼声升高,但产业链外迁多年,供应商网络、人才和工艺体系已整体转移,回流成本极高。 这种分散布局原本设想能长期维持,但中国凭借完整工业体系和强大配套能力,在全球竞争中占据关键位置,改变了原有分工优势。发达国家曾经依赖的模式,在面对这个统一工业体时,优势不再稳固。金融可以膨胀财富,但不能稳定社会;服务业能撑起GDP,却撑不起大国安全感。 发达国家当年推动去工业化,是在利润最大化和风险分散逻辑下的选择。他们清楚制造业的价值,但更清楚利润在价值链哪个环节结算。这种模式在特定时期有效,却未预料到中国作为统一工业体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