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傅斯年给陈寅恪夫妇写信,叮嘱他们抓紧时间南下。对此,陈寅恪夫人唐筼,动了心,想要收拾行李南下。但是陈寅恪却说“我坚决不去。 唐筼的手顿在叠了一半的长衫上,回头看着坐在藤椅上的丈夫,眼底藏着掩不住的焦灼。 她太清楚傅斯年的心意,也懂这封信里藏着的紧迫,彼时傅斯年已赴台筹建台湾大学,念着与陈寅恪数十年的交情,念着他目疾缠身、行动不便,才一遍遍催着南下,甚至在信里写好了接应的路线,连随行的书箱该如何安置都考虑得周全。 唐筼自嫁与陈寅恪,跟着他辗转北平、昆明、成都,半生都在躲避战乱,她的身体本就孱弱,常年受心脏病困扰,一路的舟车劳顿于她而言已是难事,更遑论对视力仅剩微光的陈寅恪,那趟南下的路,光是想想就让她心里发慌。 可她更怕的是时局未定,怕留在北平的日子里有未知的风险,怕丈夫耗费半生的学术研究,到头来连一方安稳的书桌都寻不到。 她走到陈寅恪身边,轻轻抚过他放在桌案上的手,那双手写过无数锦绣文章,校过无数古籍善本,此刻却攥着信纸。“孟真待你这般诚心,南下的路他都安排妥当了,台湾那边有安稳的住处,有齐全的医馆,你这眼睛,还有我的身子,总好过在这儿担惊受怕。” 唐筼的声音放得轻,带着几分恳求,她翻出压在箱底的药瓶,倒出两粒药片递过去,“何况你的那些书,我们慢慢搬,总能都带走的。” 陈寅恪抬手推开了药瓶,目光落在窗户外的清华园方向,那里有他耕耘了数十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他翻遍了的藏书楼,语气里没有半分迟疑,反倒带着几分执拗。 “我的书搬不走,我的根也搬不走。”他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我研究的是魏晋南北朝史,是隋唐典章,是敦煌文书,这些东西的根,在北方的碑刻里,在北平的藏书楼里,在中原的故土里,到了台湾,对着那些翻刻的典籍,我还能做什么研究?” 他不是不知傅斯年的好意,也不是不懂妻子的担忧,只是于他而言,文人做学问,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寻章摘句,而是扎根在这片土地的文脉里,离开这方水土,那些古籍、碑刻、风土人情,便都成了纸上的空谈,失了最真实的意涵。 唐筼望着丈夫的侧脸,忽然红了眼眶。她嫁给他三十余年,太懂他对学术的执念。 陈寅恪出身义宁陈氏,家学渊源,自少年时便游学海外,却始终记着自己是华夏学人,归国后便一头扎进国学研究,哪怕抗战时期躲在昆明的茅草屋里,哪怕目疾日渐加重,靠着口述让助手记录,也从未停下笔耕。 他的一生,都与这片土地的文脉紧紧缠在一起,北平的一砖一瓦,江南的一草一木,都藏在他的研究里,这样的人,又怎会愿意远走他乡,做个无根的学人? 彼时的陈寅恪,左眼早已失明,右眼的视力也仅剩0.1,连看书都要凑到眼前,靠着放大镜一字一字地辨认。他不是没有想过南下的难处,只是这些难处,在故土的文脉面前,都成了次要的。 他跟唐筼说,北平是他治学多年的地方,这里有他熟悉的师友,有他翻遍的藏书,哪怕时局再难,只要有一方书桌,他就能继续做学问。他甚至已经想好了,若是日后日子艰难,便闭门著书,把自己半生的研究都整理出来,留给后世。 傅斯年收到陈寅恪的回信后,又接连写了几封信来劝,甚至托人带来了机票,可陈寅恪始终婉拒,只是在信里对傅斯年说:“君为友谋,甚感至意,然我意已决,不拟南下。”他的这份决绝,不是意气用事,而是一位学人对故土的坚守,对学术的初心。 唐筼看着丈夫心意已决,终究是收起了行囊,默默转身去收拾书桌,把散落的古籍一一归置,她懂了,丈夫的安稳,从来都不是在安稳的住处里,而是在能让他安心做学问的故土上。 往后的日子里,陈寅恪留在北平,后执教于中山大学,哪怕后来双目完全失明,哪怕生活几经波折,也始终笔耕不辍,写下了《柳如是别传》等传世巨著。 他用一生的行动,诠释了何为华夏学人的风骨,学问可以无疆,但学人必有根,这根,扎在故土的文脉里,扎在对这片土地的眷恋里,从未动摇。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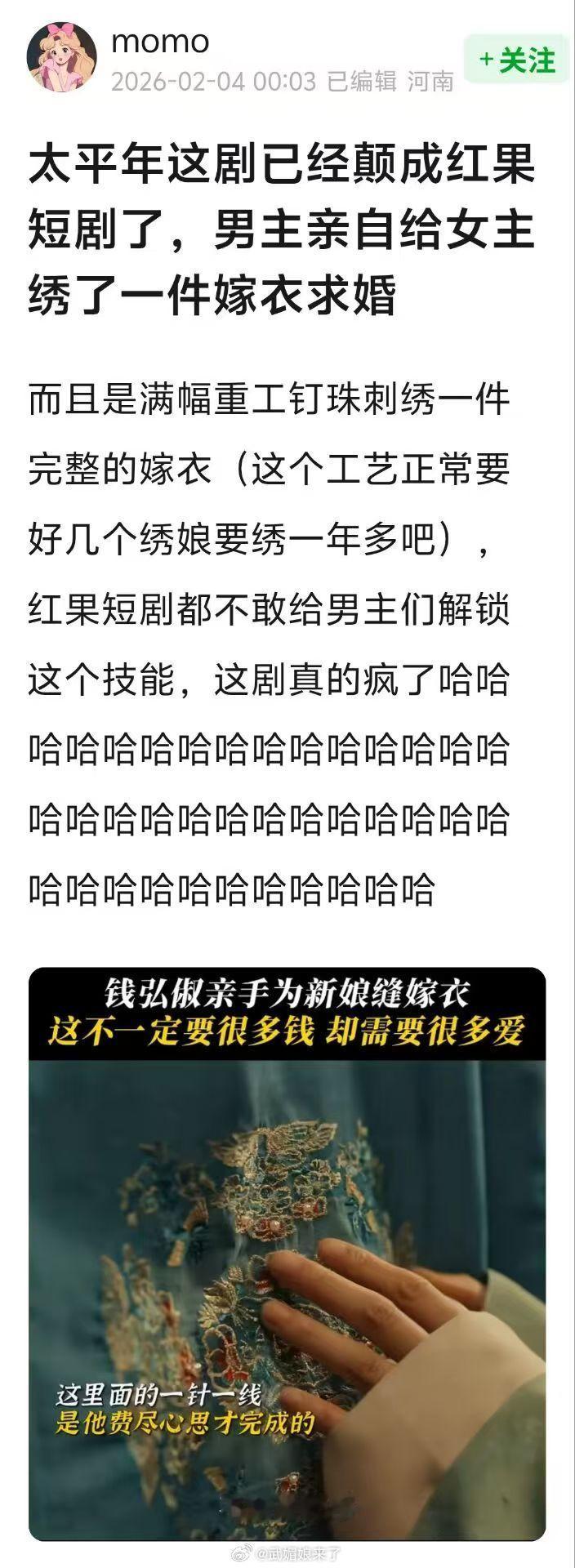




![清朝的汉人女子悲惨到极致[哭哭]据可靠的历史记载,这是清末一位青楼女子,她看](http://image.uczzd.cn/8070208966185951285.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