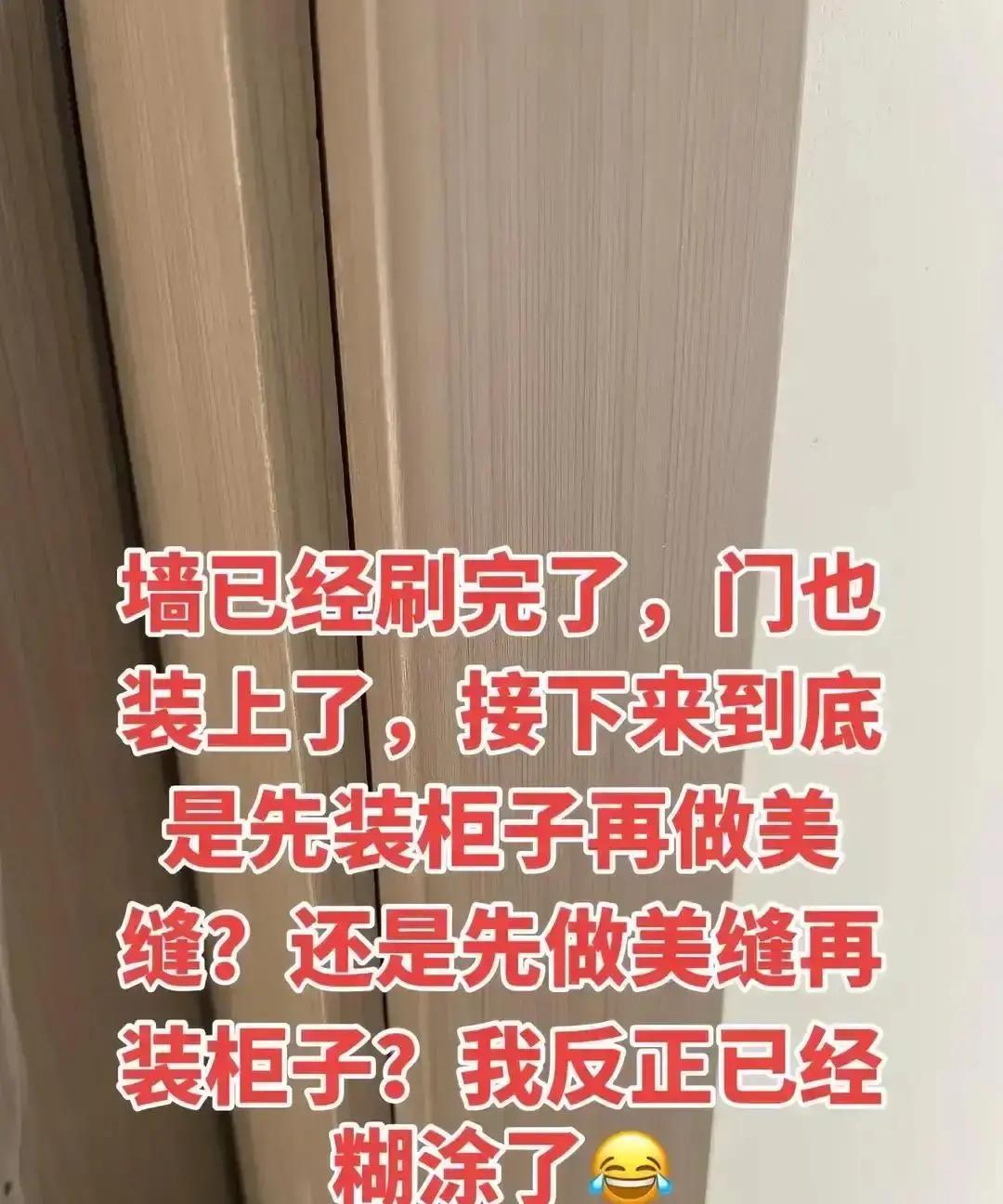我在卧室换家居服时门没锁,他推门进来拿落在沙发的领带,我慌忙扯过抱枕挡在身前:“说了非工作别进我房间!”他把领带扔桌上笑:“协议写的是‘必要时可进入’,你这算必要工作吗?”我抱着抱枕往后退半步,后背抵到衣柜门才停下。 和他签协议那天就说好,分房睡,非必要不干涉彼此空间——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今天换家居服时顺手搭在门把上的锁没扣紧,布料摩擦的窸窣声还没停,卧室门就被“咔哒”一声推开。 他探进半个身子,目光扫过沙发,径直走向我床边的矮桌——领带昨晚落在这儿了,深灰色,带着他常用的雪松味古龙水。 我吓得手一抖,刚脱下的针织衫滑到地上,条件反射捞起床尾的抱枕死死按在胸前,布料上还留着阳光晒过的暖烘烘的味道。 “说了非工作别进我房间!”声音比预想的尖,带着没藏住的慌。 他捏着领带的手顿了顿,抬眼时嘴角勾着笑,把领带往桌上一扔,布料滑过木质桌面发出轻响:“协议写的是‘必要时可进入’,你这算必要工作吗?” 我抱着抱枕往后退,脚后跟撞到衣柜门“咚”一声,冰凉的木皮贴着后背,才惊觉自己退无可退。 他的目光从抱枕移到我光裸的脚踝,又落回我泛红的耳根,那笑意淡了点,却多了点说不清的探究——像在看什么稀奇物件。 协议里的“必要”到底怎么算?他拿领带算必要,我换衣服时被撞见算谁的“不必要”? 后来我才想起,他今早有个重要会议,七点就得出门,这会儿估计是急着走,没顾上敲门——可协议里明明也写了“进入前需敲门”,他怎么偏偏忘了这一条? 我对这扇门的锁特别执着,是因为上一段感情里,前任总不打招呼闯进我房间,翻我日记,动我东西,最后闹到不欢而散;所以这次签协议,我把“边界”两个字圈了又圈,以为白纸黑字能挡住所有不自在,可他刚才那一眼,还是让我像被针扎似的浑身发紧。 他没再说话,捡起领带转身带上门,“咔哒”声比刚才轻了些,可我抱着抱枕站在原地,胸口还在砰砰跳。 大概以后换衣服,不光要锁门,还得把钥匙揣兜里——人心这东西,哪是协议能框住的? 地上的针织衫还皱着,抱枕被我攥得变了形,阳光从窗帘缝里斜进来,在领带的深灰色布料上投下一小片光斑,雪松味混着阳光的味道,在空气里慢慢散开,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又像什么都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