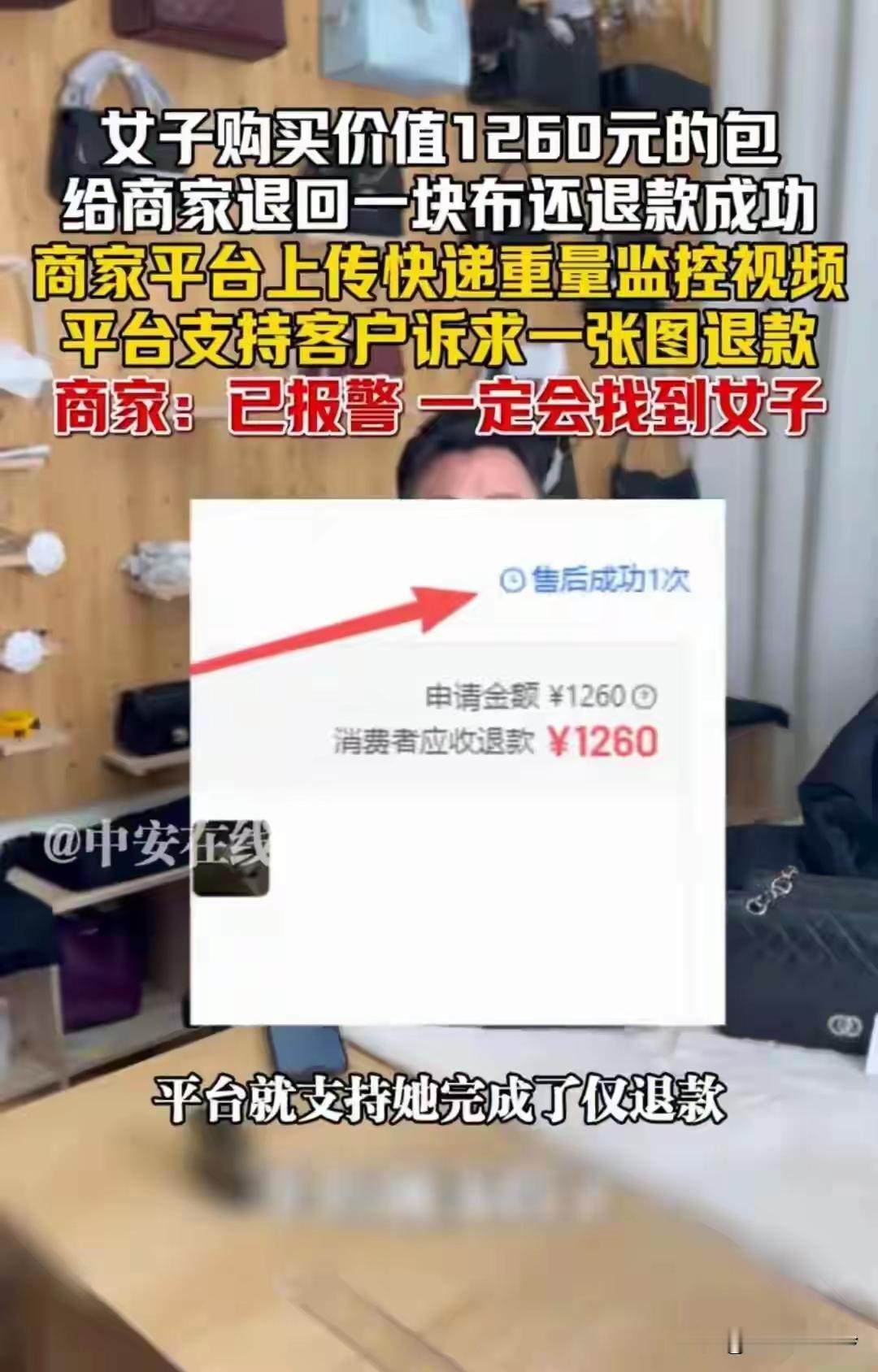昨天,厅长大舅哥破天荒地走进我的小公司,正碰上我和两个合作商在谈业务。我向他们介绍了大舅哥后,让他们十分惊讶!两个合作商是亲兄弟,姓赵,跟我合作三年了,平时都称呼我“张总”,说话办事都挺实在。 昨天下午三点,三十平米的办公室里空调正嗡嗡响,我和赵姓兄弟俩趴在会议桌上改合同,鼻尖绕着打印机刚吐出的墨香。 玻璃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时,赵大哥手里的黑色水笔突然顿住——门口站着的人,灰夹克袖口磨出细毛,却挺着我再熟悉不过的、属于机关大院的脊背。 “介绍下,”我赶紧起身,手在裤缝上蹭了蹭,“这是我爱人的哥哥,刚顺路过来。” 赵小弟“嘶”了声,手里的合同页角被捏出褶子:“张总您大舅哥是…?” 我没接话,只看见大舅哥把手里的牛皮纸袋往桌上一放,露出里面六个玻璃瓶——是我妈上周托他带的老家辣酱,瓶身还沾着快递贴的 residue。 “别拘束,”他冲赵兄弟俩摆摆手,目光扫过桌上的合同,“我就是送东西,你们谈你们的。” 赵大哥到底是见过世面的,立刻把刚泡好的菊花茶往他面前推:“领导喝茶,我们跟张总合作三年,他这人实在,合同细节我们都信得过。” 大舅哥端起杯子没喝,反而指着合同第5条付款周期:“这条90天太长了,小张公司刚起步,你们得再商量——他那点家底,我还不清楚?” 我后背猛地一僵。结婚五年,这位当厅长的大舅哥除了过年聚餐,从没踏足过我的小公司,更别提干涉我的生意。 赵小弟眼睛亮了亮,用笔杆敲着桌面:“领导说的是!我们哥俩也觉得该灵活点,要不就60天?” “别叫领导,”大舅哥把茶杯往中间推了推,瓶底在桌上磕出轻响,“我就是个送辣酱的大舅哥。倒是你们,跟小张合作三年还叫‘张总’?” 赵大哥愣了愣,突然笑出声:“那以后叫‘老张’?我们还以为厅长的亲戚多有架子,没想到比我们跑业务的还实在。” 我这才注意到,大舅哥夹克第二颗纽扣松了线头,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棉毛衫——原来他根本没穿西装,那双总在文件上签字的手,此刻正笨拙地拧开辣酱瓶盖子。 后来赵小弟私下跟我说:“老张,你藏得够深啊!但说实话,要不是你大舅哥主动提现金流,我们还真没意识到你资金周转这么紧。” 是呢,我从没跟合作商提过家里有个当厅长的亲戚,就怕他们觉得我想走捷径;可我也忘了,真正的亲近,从来不是摆架子,而是有人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用一句“他那点家底我清楚”,替你说句实在话。 合同最终签在45天付款周期上,赵大哥拍着我肩膀说“以后有事别硬扛”时,夕阳正从百叶窗缝里漏进来,在大舅哥带来的辣酱瓶上淌成金红色。 现在那瓶辣酱就摆在我办公桌最显眼的位置,每次看到松了线头的纽扣印,总会想起赵小弟的话:原来人和人的信任,从来不是靠身份标签撑起来的,而是你知道有人在你身后,却依然愿意和你站在同一张桌子前,一笔一画地磨合同。 你说,这世上最难得的,是不是那些愿意把“厅长”身份藏进夹克衫里,只做你“送辣酱的大舅哥”的人? 玻璃门外的梧桐叶还在往下掉,焦糊味混着辣椒的辛香飘进来,空调嗡嗡声好像都柔和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