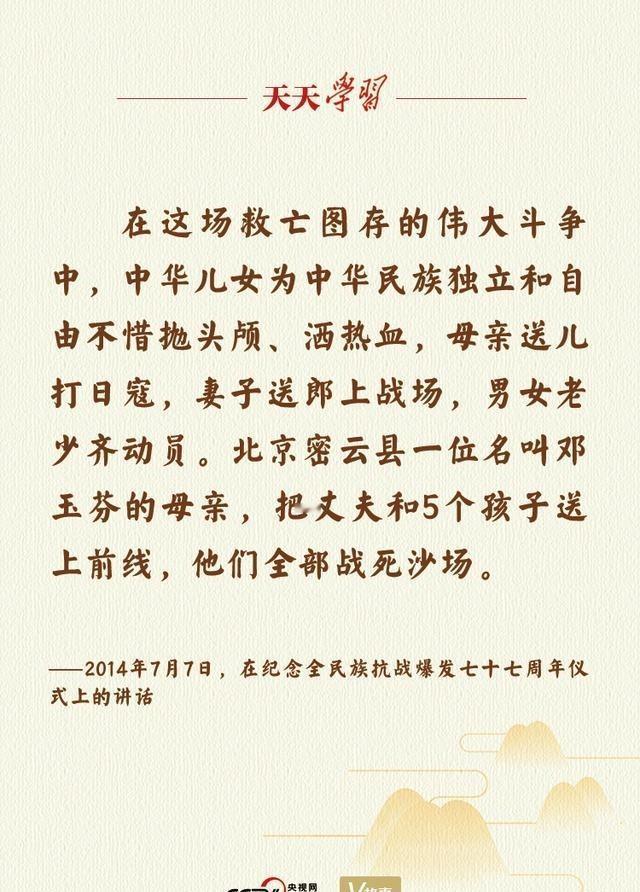1949年秋天,密云猪头岭村的邓玉芬正在地里收红薯。58岁的她腰弯得很低,手上全是泥,突然听见有人喊:“你家永兴回来了!”邓玉芬拔腿往家跑,六年了,她以为七个儿子全死在战场上,现在有人说老三回来了?会不会是哪个骗子冒充的? 跑着跑着,鞋上的泥都甩飞了,裤脚也被路边的草划开了口子。 说起邓玉芬这老太太,得从头捋捋。她1891年出生在密云水泉峪村,那地方山高路陡,穷得叮当响,从小就跟着爹妈刨食吃。长大嫁到张家坟村,任宗武那汉子老实巴交,两人租人家几亩薄地,勉强养活七个小子。天天起早贪黑,锅里就那点玉米糊,冬天裹破棉袄,夏天晒得皮黑。1933年古北口一仗打输,日军就把密云外头划进伪满洲国,村里人见日本人得鞠躬哈腰,不然就挨揍。邓玉芬一家没辙,带着小崽子挪到猪头岭山上开荒,石头地刨半天出不了把土,野菜树皮凑合着咽。 到1940年,八路军第十团进山建根据地,战士来村里讲打鬼子的事儿,邓玉芬听得直点头。她跟任宗武一合计,赶紧把在外头给人扛活的大小子永全、二小子永水叫回来,七月白河游击队刚立起来,两人就入了队。九月三小子永兴在家被人欺负得受不了,跑回来喘气,邓玉芬二话不说又把他塞进队伍。仨小子跟着部队出去转战,她在家带剩下四个,丈夫给八路军送粮背弹,自己开荒养鸡,鸡蛋全留给伤员,家里吃糠咽菜。窝棚里常住干部战士,她烧水缝衣,喂汤擦身,战士们管她叫邓妈妈。 1941年底日军搞“三光”,逼人进部落,邓玉芬不干,叫丈夫把在外干活的四小子永合、五小子永安找回,俩小子进了自卫军模范队。1942年春,抗日政府喊回山耕地,任宗武带着四五两个先上去搭窝棚,谁知马营日军偷袭,百梯子地头枪响,任宗武胸口中弹倒沟里,五小子永安机枪下没了,四小子永合被抓走。邓玉芬在外头拉种子,消息一到,人栽了跟头,醒来拉着六七两个小子就回山,扛镐头砸石头播种,粮食全支援部队。秋天大儿子永全保卫盘山中弹,肠子流一地还往前冲,抬回来时人没了。1943年夏四小子在鞍山监狱折腾死,二小子永水打仗负伤抬回家,没药治,胸口三弹头,咽气前还念部队。 1944年春日伪又扫荡,六小子跑丢,邓玉芬背着七岁小七钻山洞,几天没吃喝,小七烧得直哼哼,敌人搜上来,她撕棉袄塞孩子嘴,敌人走后孩子凉了,没名字就埋坡上。邓玉芬咬牙扛着,春播秋收做军鞋,伤员来就当自家崽子伺候。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她跪岭头磕三个头,给地下亲人报喜。1946年国民党内战起,她把六小子永恩送县支队,叮嘱立功回来。1947年八月六小子河北庄打仗立功嘉奖,1948年攻黄坨子据点壮烈牺牲。到解放前,她家九口走七个,只剩三小子音讯全无。 那年九月上旬,邓玉芬在坡上抠红薯,手泥巴糊一脸,喊声一入耳,她铁锹扔地就跑。鞋泥甩腿上,裤腿荆棘挂破,血丝渗出也不管,拐弯扶树喘,院门槛上坐个灰军装瘦汉子,眉左一道疤,小时候爬树摔的没错。三小子永兴转头喊娘,她扑上抓胳膊,袖卷起露炮弹疤,手茧子肿节。她拽进屋,绊门槛稳住,按炕沿蹲下,按膝盖问部队咋样。永兴掏纸摊炕,一张张烈士通知,大哥盘山,二哥家伤,四哥鞍山,五哥地头,六哥黄坨子,小七山洞没名。她手指捏纸边卷毛,起身取碗塞手,碗水溅炕她袖擦。永兴喝水抖下巴,她坐炕边叠手,窗风卷帘,纺车角立,门外鸡叫夕阳斜。她摸军装补丁薄,拿起纸展掌,折痕深陷。永兴说张家口伤养半年,部队批探亲,她点头添柴,火映脸。 新中国一立,猪头岭变样,土改分两亩水地,邓玉芬扛锄下田,累坐埂望山,割草喂鸡蛋托人往前线。六小子信来太原伤转院,她拆好被面缝棉袄,扣钉牢裹严交给干部。三小子胳膊使不上,她天亮熬粥,山菜篮挖满剁拌喂,夜里摸额查伤。村人上门递茶笑说补身子,她家新房和泥,灰桶搅浆淌臂。10月1日消息传村,锣鼓鞭炮响,她人群中拍鼓踩节,回家抖儿子旧衣叠炕头,夜缝袜针刺细响。问起其他小子,她喝水放碗说信部队平安。1961年春节去城开会,车颠百里握包,会场站直手叠腹,回村空手奔岭。日子过,她挥锄汗甩,1958年水库修,三小子一家参与防汛先进。1970年2月5日病重,拉干部手指路,埋路边看十团孩子。棺抬岭土堆平,碑朝南风树沙沙。清明村民鞠躬,路宽车灯扫碑,她守路通山外。 这老太太没啥大官衔,就一山村媳妇,七个崽子六个没了,小的没名,丈夫也搭上,她没哭天抢地,就这么扛着。抗日那阵,穷人抱团打鬼子,她家出人力,战士来像自家门,饭菜留着,糠菜自家咽。解放后分地盖房,她还下地,信部队不惦家。临走那句,埋路边等孩子,搁谁听都堵心。搁现在看,她那股子劲儿,家国不分家,小家碎了换大家稳。猪头岭土薄,埋人费劲,可她精神埋深,风一吹像喊别忘。村里后人修水库防汛,还搁前头干,血脉里那股不服输,传着呢。国家稳了,日子好过了,可得记着,这太平是命堆的,得珍惜。像邓玉芬这样的,千千万,搁那年头,谁家不咬牙?她就是一代表,普通得扎根土里,硬得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