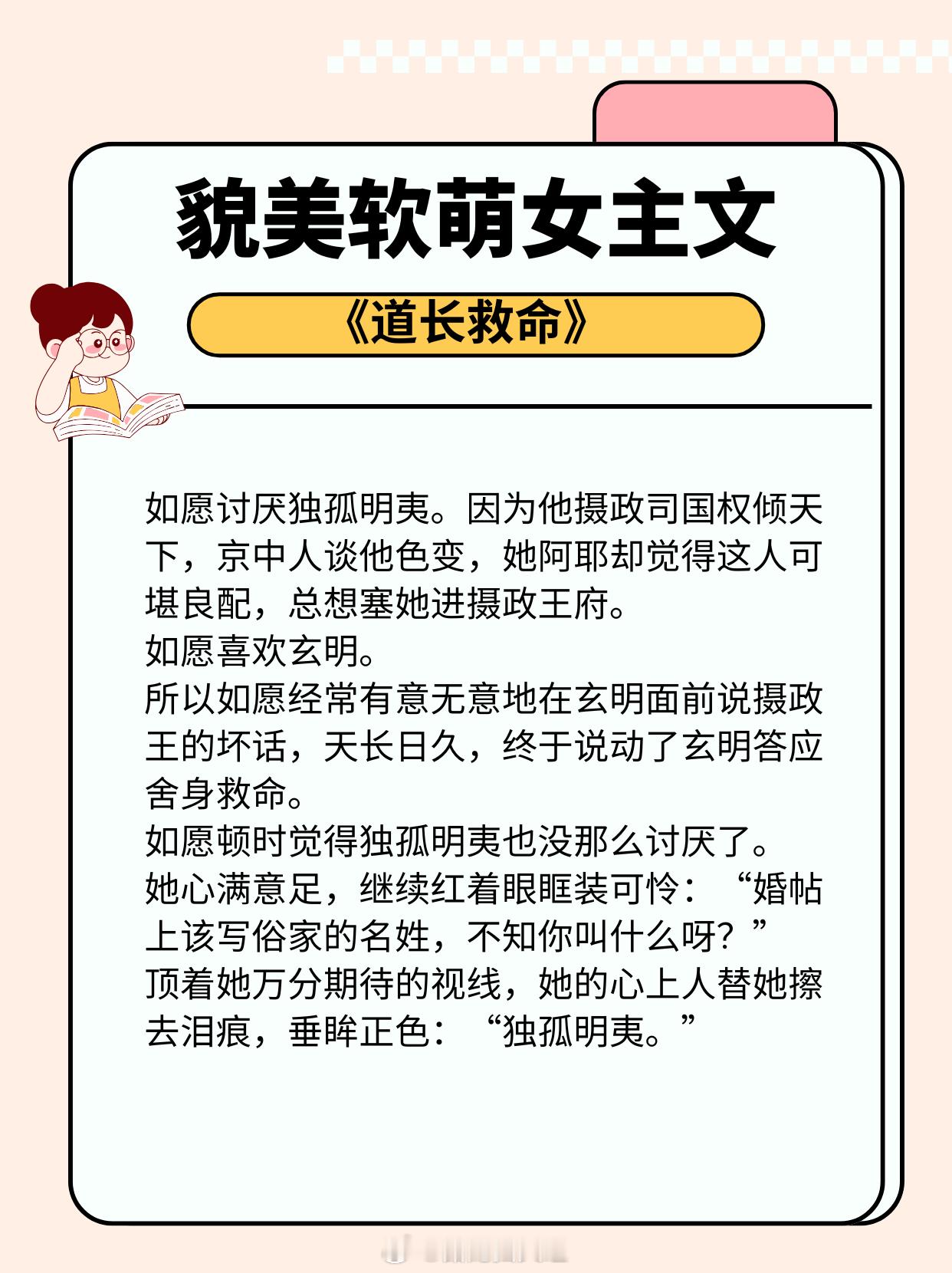我亲眼看见丈夫和那个女人在姻缘树下挂上同心结时,心里有什么东西彻底碎了。
人人都说我嫁得好,夫君是威风凛凛的镇北将军,曾当众发誓“此生唯我一人”。
可没人知道,他早在边关养了外室,孩子都会叫我娘了。
婆婆寿宴那天,我笑着接回那女人和两个孩子,满堂宾客都夸我大度。
却在最热闹时,当众摔了合卺杯。
“江闻远,你还记得成亲那日发的誓吗?”
他脸色惨白地想拉我的手,被我冷冷甩开。
“和离书我已备好,从此你我,死生不复相见。”
01
人人都说我秦舒月上辈子积了大德,这辈子才能嫁给江闻远。
他是镇北将军府的嫡子,年纪轻轻便战功赫赫,而我出身皇商秦家,似乎是再般配不过的一桩姻缘。
可他们不知道,那个曾对我许下“一生一世一双人”诺言的男人,早已在别处安置了温柔乡,甚至有了承欢膝下的儿女。
母亲很早之前就劝诫过我,她说人心若是变了,强留也无用,不如洒脱放手。
从前我总是不信,觉得江闻远是那个例外,直到我在静心寺前那棵有名的姻缘树下,亲眼看见他与另一个女子并肩而立,亲手将写有两人名字的同心结挂上枝头。
那一刻,我心中那座名为信任的高塔,轰然倒塌。
静心寺的姻缘树远近闻名,据说真心相爱的有情人若在树下祈愿,便能得到神明庇佑,白首不离。
六年前,我与江闻远也曾站在这同一棵树下,他握着我的手,目光灼灼地承诺此生唯我一人。
谁能想到,仅仅六年光景,昔日的誓言就薄得像一张被雨打湿的纸,字迹模糊,一碰就碎。
那日我是去寺中还愿的,还未走近,便瞧见了那熟悉的身影。
他身侧的女子窈窕清丽,两人低声谈笑,举止间透着说不出的亲昵,俨然是一对璧人。
过往的香客偶尔投去艳羡的目光,而我站在不远处,只觉得心口像被钝器重重砸了一下,闷痛得几乎无法呼吸。
从静心寺回来之后,那幅画面便如同烙印般刻在我的脑海里,反复浮现。
胸口像是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沉甸甸的,连带着呼吸都变得艰涩起来。
“舒月,可是身子不适?” 江闻远匆匆从外院赶来,语气依旧温柔关切,脸上寻不出一丝一毫的异样。
可他衣襟上沾染的那股淡淡的、甜腻的桂花头油香气,却是我从未用过的味道。
不必细想,我也能猜到这香气来自何处。
“无妨,只是有些疲累。” 我轻轻侧身,避开了他伸过来想要探我额头的手。
方才勉强压下的酸楚与恶心,又翻江倒海般涌了上来。
我几乎想立刻抓住他的衣襟质问,问他那六年的情分与承诺,难道就如此轻贱?问他既然心中早已有了别人,为何还能这般若无其事地对我体贴入微?
但我终究还是忍住了。
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我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足够“隆重”的场合。
三天后,婆婆的五十寿辰,或许便是个不错的时机。
“母亲寿宴的事你不必过于操劳,交给管家和下人们去张罗便是。” 他仿佛没有察觉到我刻意的疏离,依旧如往常般细心叮嘱。
“我省得的。” 我低声应了,状似无意地提起,“今日去静心寺,顺道求了一支签,竟是上上签呢。”
“静心寺”三个字出口的瞬间,我清楚地看到江闻远的神色僵了一瞬,尽管他很快就用笑容掩饰过去,敷衍地说了句“那便好”,便借口公务匆匆离去。
我能捕捉到他那一刻的慌乱与心虚,可惜,这点情绪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只漾开一圈极小的涟漪,便迅速沉没,被他完美地隐藏起来。
望着他几乎可以称得上仓皇的背影,我只觉得心底最后一点余温也凉透了。
倘若他肯坦白,哪怕只是拙劣地解释一句,我或许还会因多年情分而有所犹疑。
可他选择了沉默,选择了继续欺瞒,也就亲手斩断了所有回旋的余地。
我从未怀疑过江闻远会背叛我。
我的母亲与他的母亲是自小结识的闺中密友,同年出嫁,又同年生产。
一位是皇商夫人,一位是将军府的主母。
母亲常说,只有在江家那小子面前,我才笑得最是开怀恣意;而江夫人也总念叨,说他儿子唯有在我身侧时,才会收敛起战场带回的戾气,变得沉稳周全。
两家父亲皆因事务常年在外,两位母亲便时常凑在一处作伴,我与江闻远也因此自幼相识,可谓青梅竹马。
长大后的婚嫁,在所有人看来都是水到渠成。
外头总有些闲言碎语,说是商贾之女高攀了将门之子。
他们却不知,北疆连年战事,前线大半的粮草军需,皆由我秦家筹措运输。
陛下曾有意赐下爵位以表嘉奖,父亲却以“商人本分,不敢居功”为由婉拒,只是每年都将族中半数收益捐作军资。
成亲那日,江闻远当着满堂宾客的面郑重起誓:此生只娶秦舒月一人,绝不纳妾,永不相负。
正是因为这句誓言,我成了全皇都最令人艳羡的新妇,他也成了无数深闺女眷心中情深义重的典范。
婚后这些年,他明面上确实做到了。
虽因军务常年戍守北疆,但每次回府,总是对我呵护备至。
我不喜他饮酒,他便在府中宴客时也以茶代酒;我爱听城南书坊的评话,他哪怕被同僚调侃,也会陪我去听上一整天。
为买我随口一提的东街李记芙蓉糕,他能策马跑遍半个皇都;为寻一盒我中意的、江南新到的胭脂,他肯在天未亮时就去铺子前排队。
我曾深信,这份情意足以抵御世间所有风霜。
可如今才明白,再深的钟情,也抵不过人心易变。
他给了我身为正妻所有的体面与尊重,却把那份炽热的男女之情,连同生儿育女的期待,一并给了另一个女人。
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江闻远心中可能另有他人,是在上个月我的生辰当日。
他早早便答应要回府陪我,可我等到夜深露重,烛火都快燃尽了,也未见他的身影。
以往即便有紧急军务,他总会遣亲兵回府报个信,让我安心。
那晚却杳无音讯。
我心中不安,连夜派了好几拨家丁护卫出去寻人,自己则守在厅中,心乱如麻,生怕他在外遭遇不测。
直至次日破晓时分,我才决定亲自出门去寻。
刚走到府门前的石阶下,便与匆匆归来的他撞了个正着。
见到我,他先是一怔,随即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愧色,但很快便被疲惫掩盖。
看他安然无恙,我悬了一夜的心总算落回实处,当时只顾着庆幸,并未深思他那一闪而逝的异样。
直到他揽着我回房,从怀中取出一只锦盒作为迟来的生辰贺礼时,我的心才猛地往下一沉。
我素来不爱涂抹香粉,身上至多佩个清香囊袋,可他这次送的,偏偏是一盒质地细腻的香粉。
那香气清甜柔靡,我早已在他衣襟袖口处隐约闻到过数次,只是从前未曾多想。
而此刻,当锦盒打开,那股熟悉的甜香扑面而来时,我瞬间将其与记忆中的气味重合。
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在外应酬,沾染些脂粉气并非奇事。
可同样的香气反复出现,加之生辰之夜的莫名失约,以及这份显然未曾用心挑选的礼物,种种迹象串联起来,便由不得人不心生疑窦。
更让我脊背发凉的是,就在生辰前一日,我在西市购置绣线时,曾被一个年轻女子不小心撞到。
当时那女子连声道歉,姿态谦卑,我便未加留意。
此刻回想起来,那女子身上萦绕的,正是与这盒香粉如出一辙的甜香。
皇都街道宽阔,那女子为何偏偏绕到我身前?世间真有如此多的巧合吗?
疑心一旦生出,便如同藤蔓般疯狂滋长,必须寻个明白。
当日,我便动用了母亲留给我的人手,暗中查探。
其实江闻远并未做得十分隐秘,只是过去的我太过信任他,从未想过要去查证。
这一查,真相便赤裸裸地摊开在我面前。
那女子名叫柳依依,竟是婆婆早些年亲自安排的人。
当年江闻远初次前往北疆战场不久,婆婆便以“边关凶险,需留血脉”为由,替他收了这个房里人。
柳依依便以通房丫头的身份,随军去了北疆。
这些年,江闻远每次戍边,都是由她随行照料起居。
半年前北疆战事暂歇,大军回朝,她也随之悄无声息地回到了皇都。
起初婆婆想让她直接以妾室身份进门,被江闻远以“舒月尚未有所出,不宜刺激”为由拦下,最终只在城西的栖霞镇购置了一处宅院,将她安置在外。
想到他那些所谓“营中事务繁忙”而晚归,甚至数日不归的日子,究竟是真的忙于公务,还是去了栖霞镇的那处宅院?
每回他深夜归来,我都贴心备好温着的宵夜;每回他派人传话说要留在营中几日,我总不忘回信叮嘱他务必保重身体。
如今想来,我那些体贴与担忧,怕是徒增笑话,他哪里需要我来操心?他的另一处“家”中,自有别人将他照顾得妥帖周到。
得知柳依依存在的瞬间,我的心像是被人生生剜去一块,痛得浑身发冷。
我几乎要立刻冲到他面前,质问他为何背弃誓言,为何要如此待我。
然而,当查探的人战战兢兢地补充道,柳依依已为江闻远生下一女一子,且眼下又有了身孕时,我竟感到一阵荒唐至极的可笑。
原来,誓言的分量,承诺的珍贵,在亲生骨肉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
我慢慢地,一点点地想通了许多事。
难怪婆婆总是明里暗里关切别家子嗣,却从不催促我为江家开枝散叶。
难怪我偶尔提起想调理身体,早日生育,江闻远总是一脸疼惜地说“不忍我受孕育之苦”,说“即便没有孩子也无妨”。
原来不是不想要孩子,而是早就有了——女儿今年四岁,儿子也将满两岁。
“呕……” 听到贴身丫鬟云桑低声禀报至此,我胃里一阵剧烈翻腾,忍不住干呕起来,却什么也吐不出。
本以为他或许是一时糊涂,犯了错事。
却不想,自己竟从头至尾都活在一个精心编织的骗局里。
最令人心寒的是,婆婆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辈,平日里对我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却在我嫁入将军府不久,便亲手布下了这局棋。
若我一直未曾察觉,他们打算瞒我到何时?瞒到我人老珠黄,再也无力反抗,只能默许这一切的时候吗?
既然他们无人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那便由我来吧。
总要有个了断。
02
今日是婆婆的五十寿辰,镇北将军府邸张灯结彩,红绸高挂,贺寿的宾客如流水般涌入,门前车马络绎不绝,喧嚣鼎沸。
我身穿正红色缂丝锦裙,头戴赤金镶红宝头面,妆容得体,立在正厅门前迎客,唇边噙着恰到好处的微笑。
望着庭院中那些锦衣华服、谈笑风生的客人,心中一片冰冷地筹算着,若是趁此良辰吉日,将将军府流落在外的小主子们风风光光接回来,我那好婆婆和好夫君,会不会赞我一句“贤良大度,顾全大局”。
宴席正式开始,宾主依次落座,珍馐美馔流水般呈上,丝竹管弦之声悠扬,席间推杯换盏,恭贺之声不绝于耳。
婆婆端坐于主位之上,满面红光,我与江闻远则并肩立于她身侧,接受着众人的祝福。
人人都赞我们夫妻鹣鲽情深,是皇都里难得的神仙眷侣。
无人知晓,我此刻的心中早已激不起半分波澜,如同一口枯竭多年的深井,幽暗死寂,投石无声。
酒过三巡,席间气氛正酣。
我缓缓从江闻远身侧站起身,端起自己面前的酒杯,指尖因用力而微微发白。
清了清嗓子,我抬高了声音,那音量并不尖锐,却奇异地压过了满堂的喧闹:“今日欣逢母亲五十华诞,高朋满座,宾主尽欢,实乃我将军府一大喜事。然,妾身以为,喜事当不止于此。”
话音落下,厅内说笑声渐歇,众多目光带着疑惑与好奇,齐刷刷地聚焦在我身上。
我朝侍立在一旁的云桑略一颔首。
云桑会意,转身朝厅外示意。
很快,她便领着三个人,步履平稳地走进了这灯火辉煌、宾客云集的正厅。
为首是一名身姿窈窕的年轻女子,腹部已然高高隆起,显是有了至少五六个月的身孕。
她面容清秀,眉眼间带着一股天然的怯弱与柔顺,此刻低眉顺眼,双手紧张地交叠在身前。
她身侧跟着一个约莫四岁的小女娃,穿着崭新的粉色衫裙,脸蛋圆润白皙,像只受惊的小兔,紧紧攥着母亲的裙角,一双大眼睛怯生生地打量着周遭陌生的一切。
另有一位健壮的奶娘跟在后面,怀中抱着一个襁褓,里面的小男孩睡得正熟,那挺翘的鼻梁与抿着的嘴唇,竟与江闻远有着五六分的相似。
满堂宾客见状,先是愕然,随即交头接耳,议论声嗡嗡响起。
我面上笑容不变,声音清晰而平稳地传入每一个人耳中:“诸位贵客,容妾身介绍。这位是柳依依姑娘,当年夫君初赴北疆,母亲体恤边关艰苦,恐无人照料夫君起居,便亲自做主,将依依姑娘收在夫君房中,以通房之身随行侍奉。”
“这些年来,夫君戍守边关,征战沙场,皆是依依姑娘在身边悉心照料,不离不弃,功劳苦劳,俱是不少。”
“这一双儿女,皆是夫君血脉。女儿名唤菀菀,今年四岁;儿子名唤启儿,即将满两岁。如今依依姑娘再度有孕,为我江家开枝散叶,实属不易。此前一直居于外宅,终究名不正言不顺,亦有诸多不便。故今日,妾身便自作主张,将她们母子接回府中,从此一家团聚,共享天伦,也算为母亲寿辰,再添一重喜气。”
我的话尚未说完,厅堂内已然一片哗然。
众人面色各异,惊诧、恍然、玩味、同情的目光在我们几人身上来回逡巡。
婆婆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她先是震惊地看向我,又猛地转头去看江闻远,嘴唇哆嗦着,似乎想说什么。
但当她的目光落在那对玉雪可爱的孩子身上时,眼底深处竟飞快地掠过一丝如释重负般的欣慰,甚至极为轻微地点了点头,叹息般低语了一句:“舒月如此行事……确是贤惠,顾全了我江家体面与子嗣。”
江闻远的脸色,却在柳依依三人踏入厅堂的瞬间,骤然变得惨白如纸。
他霍然转头瞪视着我,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恐慌,以及一丝被当众撕破伪装的愤怒。
他的嘴唇颤抖着,试图开口打断我,或是解释什么,但周围宾客七嘴八舌的“恭喜”之声已如潮水般涌来,将他的声音彻底淹没。
“恭喜江将军!贺喜江将军!如今是儿女双全,后继有人啊!”
“将军府人丁兴旺,福泽绵长,真是天大的喜事!”
“江夫人如此深明大义,宽容大度,实乃当家主母之典范,令人钦佩!”
各种或真或假的恭维道贺声充斥耳膜。
江闻远在这些声音中,勉强稳住几乎要失控的神色,他深吸一口气,竟真的几步走到柳依依身边,伸手揽住了她微微颤抖的肩膀,做出了一副夫妻情深的模样,只是那笑容僵硬无比。
他的眼神却不时焦急地瞥向我,充满了不安与恳求。
我视若无睹,心如铁石。
待到这一波喧嚣略微平复,我再次举步上前,从一旁的案几上,亲手端起了一杯早已斟满的酒。
脸上的温婉笑容一点点收敛,最终化为一片冰封的平静。
我走到江闻远面前,与他仅隔三步之遥,目光如淬了寒冰的针,直直刺入他的眼底。
“夫君,妾身在此,敬你一杯。”我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骤然安静下来的大厅,“恭喜你,不仅战功彪炳,更是子嗣繁茂,家门兴盛,可谓人生圆满。”
“舒月……” 江闻远终于从最初的震惊与慌乱中找回一丝神智,他猛地松开揽着柳依依的手,急切地向前一步,想要抓住我的手腕。
我迅捷地向后退了半步,手腕一翻,杯中清澈的酒液连同那精致的瓷杯,一同摔落在大厅光洁如镜的金砖地面上。
“啪——咔嚓!”
碎裂声清脆而刺耳,像一块完整的绸缎被生生撕裂,瞬间划破了所有残余的喧闹,让整个大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宾客都屏住了呼吸,瞠目结舌地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我无视了一地的狼藉,抬眼直视着江闻远瞬间血色尽失的脸,一字一句,缓慢而清晰地问道:“江闻远,你可还记得,六年前你我成婚那日,不仅交换了婚书,更在满堂宾客与天地明月见证之下,你亲口立下的誓言?”
我的声音在落针可闻的大厅中回荡:“你说,此生唯秦舒月一妻,绝不纳妾,永不相负。若有违此誓,天人共弃。这些话,你可还记得?”
江闻远的额头上瞬间沁出了细密的冷汗,他的嘴唇哆嗦着,眼神躲闪,竟不敢与我对视:“我……舒月,你听我解释,事情并非……”
“不必解释了。”我冷冷地打断他,从袖中取出一卷早已备好的文书,当众展开,“你的解释,留给需要的人听吧。我已将你我‘和离’之事,在官府正式备案落印。从此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我秦舒月,与你江闻远,再无任何瓜葛。”
“什么?!” 江闻远如遭雷击,失声惊呼,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褪得一干二净,“和离?不!不可能!舒月,你不能……你不能这样!我不同意!”
满座宾客瞬间哗然,震惊的低语声如同水入油锅般炸开。
“和离?江夫人这是要……自请下堂?”
“竟如此决绝?连将军夫人之位都不要了?”
“江将军这事做得……唉,也难怪秦家小姐心寒至此。”
我充耳不闻那些纷杂的议论,转身走向主位上面色惨白、摇摇欲坠的婆婆。
在她面前,我缓缓跪下,姿态恭敬地磕了三个头。
“母亲。”我抬起头,语气平静无波,“多谢您这些年来对儿媳的照拂与教诲。往日年节所奉寿礼,不过是金银俗物,是儿媳不懂事,未能体察您真正所需。”
“今日,儿媳以此‘厚礼’贺寿,盼您能真心笑纳。从今往后,山高水长,望您珍重福体。也望您……永远不会后悔,当年为夫君纳下这房‘贴心人’的决定。”
婆婆颤抖着手,指着我说不出完整的话,眼中情绪复杂万分,最终只化作一声长长叹息,颓然跌坐回椅中,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舒月……你……当真无法转圜了吗?闻远他……他知道错了……”
“母亲。”我站起身,拂了拂裙摆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声音冷冽如三九寒风,“我不是您。您能为了子嗣香火,亲手为他安排妾室,容忍他外宅另立。而我,只想为自己,求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人生。这段满是算计与欺瞒的婚姻,我秦舒月,不要了。”
说完,我转身便向厅外走去,步伐稳健,背脊挺得笔直。
“舒月!舒月你等等!” 江闻远如梦初醒,猛地从巨大的打击中回过神来,他几乎是踉跄着冲了过来,不顾一切地抓住了我的胳膊,力道大得让我生疼。
他的眼中布满了血丝,充满了恐慌与哀求,再无半分平日里的沉稳将军气度:“舒月,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这就休了她!我马上把她们都送走!孩子们……孩子们也送走!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回来!你别走,求你!”
那姿态卑微至极,话语混乱不堪。
若在往日,他这般失态恳求,我或许早已心软。
可如今,听着他为了挽回我,竟能毫不犹豫地说出将亲生骨肉“送走”这样的话,我只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与更深的厌恶。
一个对为自己生育子女的女子、对亲生骨肉都能如此轻易舍弃的男人,他的承诺与忏悔,又有几分可信?
我用力甩开他的手,如同拂去什么令人不适的脏污,眼神里没有半分温度,只剩下彻底的疏离与决绝:“江闻远,事已至此,纠缠不休只会让你自己,让整个将军府,更加颜面扫地。”
“今日好歹是母亲的寿辰,是‘喜日’,我不想闹得太过难堪。”
“和离书已备,官府已备,从此你我桥归桥,路归路。你安心做你的镇北将军,享你的齐人之福,育你的儿女成群。我回我的秦家,过我自己的清净日子。我们最好——此生不复相见。”
话音落下,我不再看他瞬间灰败绝望的脸,也不再理会身后满堂的哗然与婆婆压抑的哭声,径直穿过神色各异的人群,走出了这间金碧辉煌却让我感到无比窒息的大厅。
门外阳光有些刺眼,我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脚步未曾有丝毫迟疑,一次也未回头。
03
我的婆婆待我,素来是极好的,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比对亲生女儿似乎也不差什么。
可这份“好”里,终究隔着一层。
毕竟,世上没有哪个真心疼爱女儿的母亲,会忍心亲手在女儿新婚燕尔之时,便为女婿安排别的女人,还美其名曰“为了子嗣,为了香火”。
我与江闻远成亲不过两月,戍守北疆的公公便在一次突袭中不幸战死沙场。
江闻远作为嫡子,仓促承袭了爵位与军职,不得不即刻奔赴边关,稳定军心。
婆婆心疼儿子年轻骤然担此重任,身边又无人细致照料,便瞒着我,精心挑选了几个“懂事妥帖”的丫头,悄悄送去了北疆军营。
而我那新婚才一月有余的夫君,竟也半推半就地收下了,未曾有过只言片语的反抗或告知。
北疆战事时紧时松,江闻远其间也曾数次回皇都述职或休整,可他从未对我提起过在北疆军营中,早已有人为他红袖添香,甚至生儿育女。
成亲前夜,母亲曾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舒月,闻远那孩子眼下对你是真心实意的好,娘都看在眼里。可人心隔肚皮,世事难料,这份情意能维持多久,谁也无法担保。倘若将来有一天,他变了心,或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记住,莫要一味委屈求全。秦家的女儿,不靠任何人,也能活得堂堂正正。”
那时的我,正沉浸在待嫁的喜悦与对未来的憧憬中,闻言立刻挺直了背脊,信心满满地反驳:“娘,闻远哥哥和别的男子不同!我们自幼一同长大,他是什么品性,我最清楚不过。他说过此生唯我一人,就一定会做到。我们会一直好好的,他绝不会让我伤心。”
母亲听了,只是深深地看着我,良久,才轻轻叹了口气,没再多劝,只将一个雕刻着缠枝莲纹的紫檀木小匣子塞进我手里,低声道:“若真有那么一天,你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便打开这个匣子。里面是娘为你准备的一条退路。”
知道江闻远在外蓄养外室,且已儿女双全的第三天,在极致的愤怒与心寒过后,我想起了那个被尘封在妆奁深处的紫檀木匣。
颤抖着手打开铜扣,里面并无金银珠宝,只有一封信,以及一张墨迹早已干透、签章齐全的“和离文书”。
信是母亲亲笔所写,寥寥数语,只道无论我作何选择,秦家永远是我的后盾。
而那张文书,已然具备了律法效力,只需送至官府备案,我与江闻远的夫妻关系便可就此解除。
捧着那张轻飘飘却重若千钧的纸,我的眼泪终于决堤而出,不是为逝去的感情,而是为母亲这深远的、无声的庇护与支持。
她早已为我预想到了最坏的结局,并替我扫清了障碍,让我不必在遭遇背叛时,还要徒劳地耗费心力去争取一纸自由。
父母前些年已将家中生意大半交予可靠族人打理, themselves则四处游历,寄情山水,此刻尚在江南,还不知皇都家中发生的巨变。
幸而我离家前已暗中嘱咐过府中老管家,因此当我回到秦家旧宅时,一切井然有序,仆从们恭敬如常,无人多问一句,只默默为我备好了热水、干净的寝具和可口的清粥小菜。
接连数日,我都将自己关在出阁前居住的“揽月轩”中,足不出户。
和离之事办得干脆利落,可长达近二十年的情意与六年的婚姻,要想从心底彻底剜去,又岂是易事?
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想与江闻远的过往。
那些两小无猜的嬉戏时光,少年时他为我爬树摘杏子摔破膝盖的笨拙,成亲后他每次归家带给我的北疆新奇小玩意,夜里为我细心掖好被角的温柔……
记忆越是清晰美好,对比当下的不堪就越是尖锐残忍。
想得愈多,心便愈冷。
所有的“好”,都建立在欺瞒与背叛的流沙之上,早已不值得半分留恋。
母亲说得对,变了心的人,放手就好。
可为何我已经毅然放手,斩断了一切,心口那空落落的、夹杂着钝痛的地方,却并未随之填满,反而有种茫然的虚浮?
不知独自坐了多久,直到窗外天色彻底暗沉下来,烛台上的蜡烛也燃短了一大截,我才感到一阵强烈的疲惫如潮水般袭来,眼皮沉重得抬不起来,伏在案几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这一觉睡得极不安稳,梦境光怪陆离。
一会儿是少年江闻将刚出锅的、我最爱的桂花糖藕小心吹凉,递到我嘴边,眼里盛满了星光般的笑意与宠溺。
一会儿却又见他紧紧搂着柳依依,在栖霞镇的宅院中逗弄着两个孩子,画面温馨刺眼。
我拼命呼喊,他却回头,目光冰冷陌生,斥我为何还不离去,打扰他们一家和睦。
我挣扎着想跑过去拉住他问个清楚,双腿却如同灌了铅,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浓雾里,留下我一个人站在无边无际的荒原上,寒风刺骨。
“舒月……舒月……” 似乎有人在唤我,声音遥远而模糊。
费力地睁开酸涩的双眼,视线由朦胧逐渐清晰,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张布满胡茬、眼窝深陷、憔悴不堪的脸。
是江闻远。
他身上的将军常服皱巴巴的,发髻也有些松散,哪里还有半分平日威风凛凛、仪表堂堂的模样。
乍一见到他,梦中的寒意与绝望尚未完全褪去,我心头火起,脸上自然没了好颜色,立刻扬声朝外间唤道:“云桑!云桑!”
守在门外的云桑应声疾步进来。
我看也不看江闻远,冷声吩咐:“去叫前院护院来,将这擅闯内宅的闲杂人等给我‘请’出去!传我的话,日后谁再不经通传,随意放外男进入后院,一律发卖,绝不轻饶!”
我的话既重且冷,毫不留情面。
江闻远听得分明,脸上血色又褪去几分,却并未动怒,反而向前凑近一步,声音嘶哑,带着浓重的恳求与讨好意味:“舒月,你别这样……我只是……只是想来看看你,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江将军瞒天过海,外宅藏娇,儿女成双,这般本事,怎么会是糊涂人?”我扯了扯嘴角,露出一抹毫无温度的讥诮笑意,“如今却像个登徒子般,擅闯我和离归家女子的闺房,是把脑子落在你将军府了吗?若真想见我,按着规矩,去门房递上拜帖,言明事由,我自会在前厅见你。你这般行径,传将出去,是嫌我秦舒月名声太好,还是嫌你镇北将军府的脸面丢得不够彻底?”
“舒月,我们之间……当真要如此生分,如此绝情吗?”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眼眶竟微微发红,“我知道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当时……当时是母亲以死相逼,我又年轻糊涂,半推半就……后来在北疆,是她一直悉心照料,我一时心软……可我心中最重要的,始终只有你啊!你就不能……不能看在往日情分上,再给我一次机会?”
“江将军真是好本事。”我轻轻抚平袖口的一道褶皱,语气凉薄,“一句‘年轻糊涂’、‘一时心软’,便能弄出三个活生生的孩子来。若天下男子都如你这般‘糊涂心软’,咱们大周怕是早已人满为患,日后征兵,怕是再也不用发愁兵源了。”
“舒月!你……你怎能如此说?”他像是被刺痛,又急又悔,“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打我骂我都可以!只要你能消气,能原谅我,让我做什么都行!”
“当真做什么都行?”我抬眸,终于正眼看向他,目光平静无波,像是在审视一件无关紧要的物品。
他眼中瞬间爆发出强烈的希冀之光,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看我的眼神又染上了几分从前那般的热切与专注:“当真!千真万确!只要舒月你肯回头,肯再给我一次机会,便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绝不皱一下眉头!”
“那好。”我点了点头,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谈论今日的天气,“你把柳依依,连同她所生的三个孩子,全部送走。送去哪里我不管,但必须离开皇都,离开北疆,离开一切你可能触碰到的地方。并且,立下字据,此生永不复见,永不接济,权当从未有过这些人,这些事。你的孩子,从此与你,与江家,再无瓜葛。你若能做到,或许,我还可以考虑。”
我的话音落下,室内陷入一片死寂。
江闻远脸上的希冀与热切如同被冰水泼中,瞬间冻结,而后寸寸碎裂。
他瞪大了眼睛,像是第一次认识我一般,用一种混合着震惊、失望与隐隐愤怒的眼神死死盯着我,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颤抖的声音:“舒月!你……你何时变得如此狠心绝情?那毕竟是活生生的人,是我的骨血!你从前……从前连只受伤的雀儿都要细心救治,不是这样的!”
“从前的我,确实不是这样。”我迎着他指责的目光,缓缓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晰而沉重,“可是江闻远,你先问问你自己,从前的你,是现在这副左右逢源、欺瞒发妻、儿女成群的样子吗?”
“你自己,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月下发誓‘此生唯一’的少年郎了,又凭什么要求我,必须还是当年那个傻傻信你、全心待你的秦舒月?”
或许是久坐乍起,也或许是情绪起伏,刚醒来时便有的头晕此刻更加明显,一阵阵的眩晕感袭来。
我扶住身旁的桌案边缘,稳了稳心神,已然不想再与他做任何无谓的纠缠。
他僵在原地,脸色变幻不定,显然内心在天人交战,既舍不得放弃挽回我的可能,又无法狠心答应我那“冷酷”的条件。
我不再理会他,直接对再次进来的云桑挥了挥手,语气疲惫却不容置疑:“送客。若江将军不肯自己走,就让护院‘帮’他一把。”
说罢,我转身走向内室,反手关上了房门,并将门闩轻轻落下。
隔绝了外面的一切声响。
背靠着冰凉的门板,方才强撑的力气仿佛瞬间被抽空,眩晕感更重。
我摸索着回到床边,和衣躺下,拉过锦被盖住自己。
窗外似乎隐隐传来争执与离去的脚步声,渐渐归于平静。
头脑昏沉一片,意识很快又陷入了模糊的黑暗之中。
再次醒来时,已是次日黄昏时分。
寝室内光线昏暗,只有一缕残阳的余晖透过窗棂,在地面上投下长长的、寂寥的光斑。
云桑轻手轻脚地进来,见我醒了,便低声禀报:“小姐,江将军……昨日午后一直在院中站着,任谁劝也不走,直到日头偏西,见您始终不肯再见,才……才低着头离开了。离去时,神情甚是颓丧。”
我静静地听着,心中并无半分波澜,既无快意,亦无悲悯,只有一片近乎麻木的平静。
这样也好。
只愿从此以后,江湖路远,再不相见。
我与他之间,早在寿宴那日酒盏碎裂之时,便已恩断义绝,再无转圜余地。
和离后的日子,起初过得异常缓慢而空旷。
不再需要打理将军府繁杂的内务,不再需要应付各府人情往来,也不再需要为某个人的归来或离去而牵肠挂肚。
时间忽然多出了大把,反倒让人有些无所适从。
我试着捡起出嫁前喜爱的丹青,却总是提笔忘形;想读些游记杂书打发时光,目光落在字里行间,却久久无法聚焦。
心头那片被强行挖去的空洞,似乎仍在隐隐作痛,提醒着过往的一切并非幻梦。
就在我对着窗外一树将谢未谢的海棠,怔怔出神,思索着是否该听从管家建议,去城外的别庄小住散心时,一个我从未想过会再见到的人,竟不请自来,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若不是她主动报上姓名,我几乎无法将眼前这个形容憔悴、神色仓皇的女子,与记忆中那个在将军府寿宴上虽怯弱却难掩清丽颜色的柳依依联系在一起。
她穿着一身半旧的藕荷色襦裙,发髻松散,只用一根素银簪子勉强固定,脸上未施脂粉,眼下有着浓重的青黑,更显得面色蜡黄。
最触目惊心的是,她纤细的脖颈上,竟赫然有着几道清晰可见的、深紫色的淤痕,像是被人用力掐扼所致。
而先前寿宴时她高高隆起的腹部,此刻已然平坦下去。
她整个人如同秋风里瑟瑟发抖的落叶,再无半分当日被接回将军府时,那种即将母凭子贵的隐隐期盼与柔顺风光。
见到我,她未语泪先流,“扑通”一声便直挺挺地跪在了我揽月轩冰凉的地面上,对着我重重磕下头去,声音凄切哽咽,充满了无尽的悔恨与恐惧。
“夫人!秦小姐!求求您,求求您发发慈悲,回去吧!回到将军府去吧!”
她抬起头,泪流满面,眼中是近乎绝望的哀求:“孩子……我的孩子……已经没了。是将军,他听了您的话,逼我喝下了落胎药……那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啊……”
她泣不成声,缓了好一会儿,才继续道:“菀菀和启儿,将军已经让人将他们的名帖,都过到您的名下了!以后他们就是您的孩子,尊您为嫡母!妾身再也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只求您能回去,只要您肯回去,将军一定会回心转意,这个家才能像个家啊!求您了!”
她说着,竟膝行上前,试图抓住我的裙摆,那姿态卑微到了尘埃里。
我后退一步,避开了她的触碰,眉头微蹙。
她见我后退,哭得更加凄惨,断断续续地诉说着我离开后,将军府里发生的变故:“您走之后,将军就像是彻底变了一个人……他整日酗酒,动不动就大发雷霆。他怪我……怪我将事情闹到了明处,怪我不该出现在寿宴上,更怪我……怪我当年不该跟着他去北疆,不该生下孩子……”
“前几日,他醉酒回来,竟……竟掐住我的脖子,说要掐死我,说都是我害得他失去了您……他还说,要把菀菀和启儿都送到远远的庄子上,或者……或者干脆送给不知底细的人家,免得他们碍眼,妨碍他求您回心转意……”
“夫人,秦小姐!”她再次重重磕头,额头碰在青砖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我知道我对不起您,我罪该万死!可孩子……菀菀和启儿是无辜的啊!他们身上流着将军的血,也是我的命根子……那是我在北疆苦寒之地,拼了半条命才生下来,精心养到这么大的骨肉啊!求您看在孩子年幼懵懂的份上,可怜可怜他们,回去吧!只有您回去了,将军才能恢复正常,孩子们才有一条活路啊!”
她的哭声凄厉,话语中的信息更是令人心惊。
我没想到江闻远在我决绝离开后,竟会如此失控,甚至迁怒于柳依依和亲生子女。
逼人落胎,欲将稚子送走,这已不仅仅是薄情,几近冷酷与疯狂了。
然而,惊诧之余,涌上心头的,却并非同情,而是一种更深沉的疲惫与疏离。
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他与子女间的冷酷处置,听在她耳中,只觉像是一场与己无关的、荒诞的闹剧。
我看着她哭得几乎要背过气去的模样,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涟漪:“柳姑娘,我想你弄错了两件事。”
“第一,我与江闻远已经和离,有官府文书为证。将军府的一切,无论人、事、物,都早已与我秦舒月毫无干系。你们是聚是散,是恩是怨,是生是死,皆由你们自己承担,轮不到我来过问,更谈不上‘回去’。”
“第二,”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她颈间的淤痕,语气依旧淡漠,“你的孩子是否无辜,你是否拼了命生下他们,那是你与江闻远之间的事。从你决定接受他母亲安排,随他去北疆,并为他生儿育女那一刻起,你就该想到,将自己的命运与喜怒全然系于一个男人身上,终有一日,或许会面临今日这般境地。路是自己选的,如今这般苦果,自然也需你自己咽下。”
我的话如同冰锥,刺得柳依依浑身一颤,哭声戛然而止,只睁大了一双空洞绝望的眼睛,失神地望着我,仿佛无法理解我为何如此铁石心肠。
室内一片寂静,只有她偶尔压抑不住的抽噎声。
良久,她像是终于认清了我绝不会心软的事实,眼中最后一点光亮也熄灭了。
她慢慢地、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身形摇晃,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不再哭泣,也不再哀求,只是用一种死寂般的眼神看了我最后一眼,那眼神里混杂着绝望、认命,以及一丝极其复杂的、难以言喻的情绪。
她转过身,步履蹒跚地向着门外走去,背影萧索得如同秋日最后一枚枯叶。
就在她的身影即将消失在门槛外的暮色中时,她忽然停住了脚步,没有回头,只是用那种嘶哑的、如同砂纸摩擦般的声音,轻轻说了一句:“秦小姐,您以为离开将军府,斩断关系,便能彻底解脱,置身事外了吗?”
我眉头微动,没有接话。
她低低地、近乎呢喃地继续道,那话语却带着一股冰冷的寒意,直透人心:“将军昨夜……连夜写了一道奏疏,已经递进宫去了……听书房伺候的小厮酒醉后漏出的口风,那奏疏里提及……提及当年北疆粮饷调度,似乎……与秦老爷有些关联,言辞之间,颇多含糊暗示之处……”
“您觉得,以将军如今的心性,在您这里碰壁之后,真的会轻易放过您,放过秦家吗?”
话音落下,她不再停留,身影彻底融入了门外渐浓的夜色之中。
只留下那几句轻飘飘却又重若千钧的话,如同投入静潭的石子,在我骤然收缩的心湖里,激起了一层又一层的冰冷涟漪。
轩内烛火微微跳动,将我的影子拉长,投在墙壁上,摇曳不定。
窗外,最后一线天光也被夜幕吞噬,无边的黑暗,无声地笼罩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