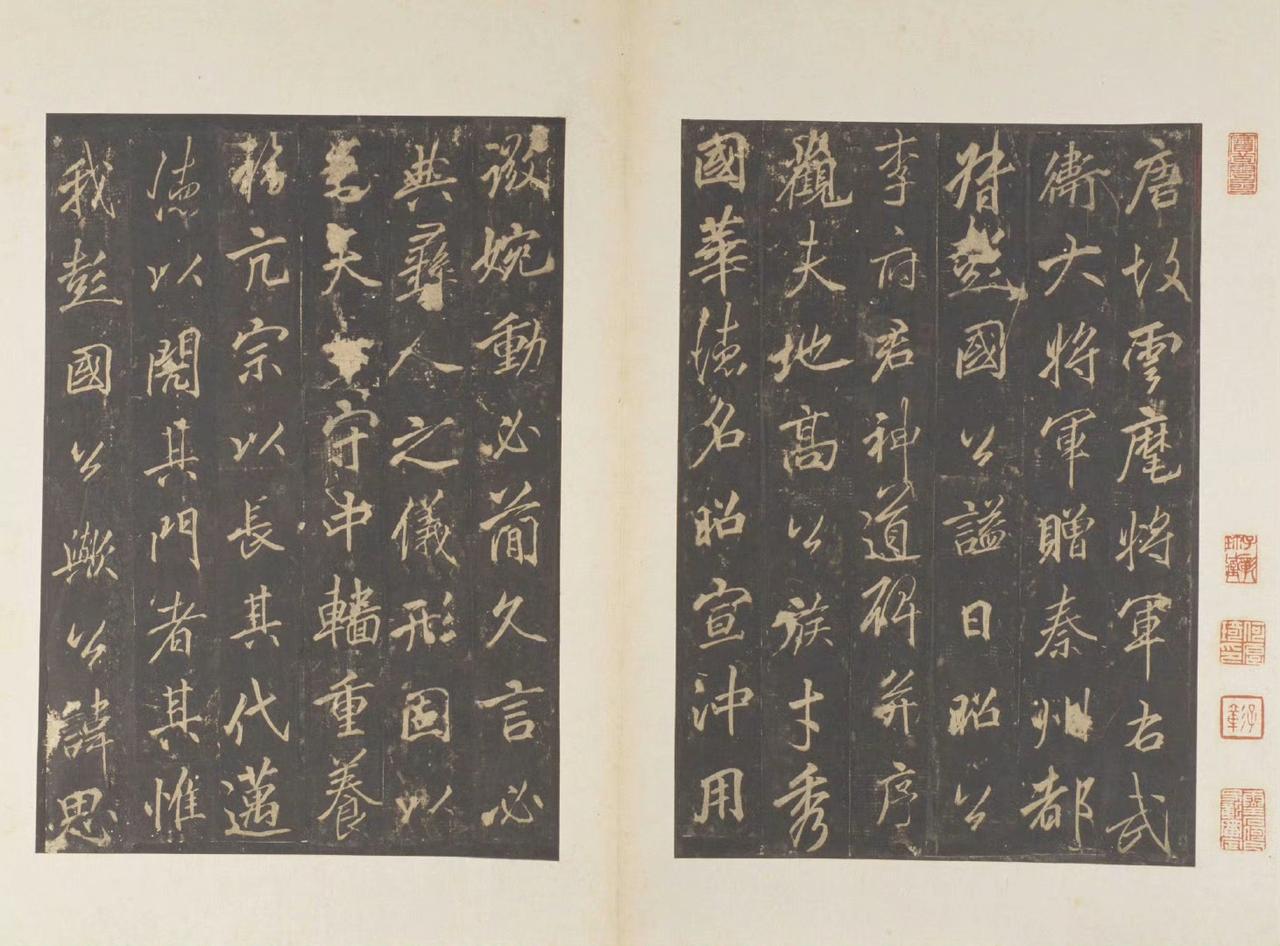米山镇的老街走到头,铁佛寺的山门就藏在几棵老槐树后头。朱漆大门掉了半扇,剩下的那扇歪在门轴上,风一吹就吱呀响,像谁在嗓子眼儿里卡着口痰。门楣上的"铁佛寺"三个字被雨水泡得发胀,笔画边缘卷了边,最底下的"寺"字少了最后一横,是民国时被流弹崩的,现在还能摸到木头茬子。


跨进门槛的瞬间,一股子潮味裹着香火气扑过来,呛得人直皱眉。供参观的走道窄得厉害,两个人并排走得侧着身子,墙根处的青砖被踩得发亮,能照见人影。守寺的老李说这走道原是条排水沟,后来填了砖改成路,所以总泛着潮气,墙角的霉斑长得像片乌云,去年刷了三遍石灰,今年又冒出来了。

二十四诸天彩塑就立在走道尽头的佛台上,离得老远只能看见个模糊的轮廓。最东头的那位天神披着铠甲,头盔上的红缨早就没了,露出里面的铁丝架,像插着几根锈针。老李说这铁丝是明代的,当年工匠从晋城的铁矿里挑的好料,现在用磁铁去吸,还能听见滋滋的响。有回文物局的人来检测,说铁丝的含碳量比现在的钢筋还高,老李听了直撇嘴,说再结实也架不住麻雀啄,现在铠甲的铁片上尽是小坑,是麻雀的杰作。

第二尊塑像的衣摆垂得老长,褶子打得密,像真的绸缎堆在那儿。走近了才看清,褶子里缠着些细铁丝,最细的比绣花针还软,老李用手捋过,说这是当年工匠用镊子盘的,现在还能活动。去年有个绣娘来,对着褶子绣了半个月,说比苏绣的针法还复杂,现在那幅绣品挂在镇文化站,比寺里的香火还旺。

中间那尊天神的脸圆乎乎的,脸颊上的红晕褪得只剩个淡印子,露出底下的黄土色。老李说这是用小米面调的颜料,雨水一泡就掉,前几年试着补了补,用的是现在的丙烯颜料,结果新的比旧的还先掉色,现在索性就让它那么淡着,倒像天神害了羞。

西边那尊塑像的手握着根法杖,杖头的宝珠掉了,露出里面的铁球,锈得发红。老李说那宝珠原是琉璃的,抗战时被鬼子抠走了,现在铁球上的锈掉在地上,像撒了把红土。有回他扫院子,扫出块碎琉璃,透着蓝,该是宝珠的碴子,现在用布包着,藏在佛台的抽屉里,谁也不给看。

佛台的砖缝里长出几丛瓦松,最肥的那棵从一尊塑像的脚边钻出来,把砖顶得翘了起来。老李想拔,又怕碰坏塑像,只好用剪刀剪,剪下来的瓦松汁是白的,像牛奶,他尝过,涩得舌头发麻。去年有个中医来看,说这瓦松能入药,老李就留了几棵,现在长在窗台上的花盆里,倒比寺里的香火旺。

光线暗得厉害,后墙的窗棂糊着纸,破了好几个洞,阳光漏进来,在塑像身上投下细碎的光斑。老李说这光得赶在晌午看,那会儿光斑正好落在中间那尊天神的眉心,像点了颗朱砂。有回一个摄影师蹲在走道里等了三天,才拍成那张照片,现在放大了挂在寺门口,倒比"铁佛寺"的牌子还显眼。

最西头的塑像缺了只耳朵,是文革时被红卫兵砸的,现在用水泥补了个疙瘩,远看像贴了块膏药。老李说耳朵里原来藏着个小铁盒,装着些经文,砸耳朵的时候掉了出来,被个老汉捡走了,后来老汉的孙子考上了大学,说这是天神显灵,现在每年都来寺里烧香,给补的耳朵上挂块红布,倒比原来的还精神。

走道尽头的墙面上有个小孔,是前几年特意打的,为了让外面的光透进来照塑像。老李每天中午都要蹲在孔边看,说光移动的速度比钟表还准,到了酉时准会照在最东头那尊天神的脚边。有回他孙子放学晚了,就跟着光斑回家,说比路灯还靠谱。

离开的时候,老李正踩着凳子给塑像掸灰,鸡毛掸子举得老高,生怕碰掉点啥。他说这些塑像看着硬邦邦的,其实比谁都娇气,去年下暴雨,有尊塑像的肩膀渗了水,长出层白毛,他用棉签蘸着白酒擦了三天才擦掉。现在每尊塑像的脚边都摆着个小碟子,盛着石灰,吸潮气用的,老李说这是他爷爷传的法子,比啥高科技都管用。

走出寺门时,老街的槐花开得正旺,落了一地白。老李锁门的声响在巷子里荡开,惊起几只麻雀,扑棱棱掠过寺顶,翅膀扫过那扇破窗棂,带起的灰落在塑像的铠甲上——那灰里,藏着明代的铁屑,藏着清代的香灰,藏着民国的弹痕,也藏着老李每天擦像时掉的头发丝,混在一起,倒比任何经文都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