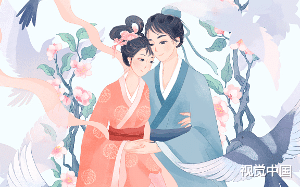我们驭兽一族在成年礼前,都必须找好灵兽人选进行结契,否则无法活过成年。
我在奴隶市场救下一条沦为奴隶的蛇兽,精心照顾,约定结契。
可在成年礼的前一天,他却将我下药打晕关在柴房,害我诅咒爆发而死。
重活一次,我抱起撞到脚边的小猫兽,踹开蛇兽伸过来的脏手。
「忘恩负义的东西,不配入我家的门!」

1
我是宋家二小姐。
因为受到一位古时灵兽大能诅咒,我们驭兽一族的血脉必须在成年之前,得到一位拥有灵兽血脉的兽人认可,借助契约解除诅咒,否则就会在成年当晚因诅咒爆发身亡。
父亲本打算为我挑选合适的灵兽人联姻。
然而在那之前,我误入奴隶市场,买下一位蛇族兽人奴隶。
席地而坐的蛇兽撞入我眼中,冷调的金色蛇瞳懒散垂着,跌入尘埃而不失风骨,叫人难免心生欣赏。
他的名字是霖祀。
于是我买下他,给他治疗。
他伤得很重,连本源也有缺损,虽不伤性命,但实力大减,极难治愈。
当然,这对我这个嫡系小姐不算什么,我的私库里的好东西足够多。
我最初只是把人丢给了府医,没太关注。
只是霖祀伤势稍缓之后,便以报恩为名主动向我示好,精巧的木雕,漂亮的首饰,午夜因为我的一次抱怨去寻竹苑的清酒,早起特意绕远去买点香斋的限量糕点一样一样悄悄摆在我门口——他向我许诺永不背叛。
我快就要成年了,还没找到合适的兽人,父亲为这件事专程回来,考校了他的能力,又因奴隶身份知根知底,与他夜谈。
父亲的意思我明白,我并不排斥。
这样,霖祀作为我的契约兽人,我未来的丈夫,当然要尽早治好,好以最好的状态赶上我的成人礼。
父亲培养他,于是他开始早出晚归,哄我的眼神中满是对未来的期盼。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话里的美好未来,没有半分是面向我的祝愿。
直到成年的前一天晚上,我被他骗到柴房打晕关押,错过我一生一次成人礼。
他在我身上下了药,即便醒来,我也无法抬起力气尽失的手腕,连声音都变得模糊微小,无法求救。
沉睡的诅咒在我体内炸裂,灼热的痛感和晕眩如潮水侵袭,对肢体的控制力缓慢逝去,连带着深入骨髓的酸软。
黑暗的柴房吞噬了颤抖难辨的尖叫,我不知道自己挣扎了多久,指甲翻开,血肉模糊。
我的嗓子喊哑了,一口一口的咳出鲜血。
最后,在绵延不绝的痛苦折磨中,我的意识逐渐陷入昏黑。
从始至终没有人发现我,我仿佛被遗忘在世界之外。
在死去的幻影中,我的灵魂昏沉着轻飘飘的离开身体。
我看见一个人被我的病弱庶妹扯着手腕,来回匆匆寻找我的踪迹,耳后未褪的黑鳞映出火焰的光。
她叫他「林藤」。
我看他的神情动作,身形衣服,分明是霖祀。
霖祀带着笑,视线全神贯注的落在她身上。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夹杂着偏执的爱意和得意。

2
意识从黑暗中归拢,我半眯着眼睛,尖锐的疼痛仿佛还在骨头缝里混乱流淌,随即传来诡异的失重和倒错感。
「这货底子不错,算是个难得的硬骨头,小姐您要真想要……」
谄媚又阴郁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难听吵闹的要命。
我抬手按住胀痛的太阳穴,从反胃的恶心感中努力抬眼,直直对上了一张无比熟悉的脸。
铮铮风骨,身形挺拔,在一片浑浊之中仿佛不染尘埃。
当年我就是被这样的形貌迷了眼,给自己引来了杀身祸害。
如今撇去惊鸿一瞥的滤镜,我看见他刻意偏着角度抬起的下巴,眼神一瞬又一瞬的飘向我的方向,竟是有意关注我的动向。
家逢大变沦落为最底层的奴隶,能有心为自己谋划自救,当然会引人欣赏。
救到身边做个下属幕僚也算捡漏,只可惜——这是个会恩将仇报的白眼狼。
我怎么可能重蹈覆辙?
我本转身欲走,一团脏兮兮的小东西扑通撞上了我的脚腕。
「这个也是你家的?」
我眯着眼细看,在那乱七八糟的毛里看出一只沾了点儿黄尖儿的白毛耳朵来。
「这个啊……」
奴隶贩子看了一眼,又看看我被污渍沾上的裤脚,诚惶诚恐的把腰弯的更低。
「是的是的,小姐息怒,这猫崽子不懂事,弄脏了您的衣服,我这就处理!」
他做势要把猫崽子踢开,但它死死扒住了我的鞋,奴隶贩子就无从下手。
「这样吧,您看看别的货,咱给您打个折,」他束手无措,慌忙笑笑,不敢真的伸手碰到我,「咱小本生意,没管好手里的货的确是咱的错,也劳您别太怪罪。」
「无妨,挑几个健壮好管的,送到宋府上去,」我从旁边的铺子上捡了个竹篮子,随手签了张证明,「拿这张条子给管事,他会把账结给你。」
从这些人手上讨折扣可不容易,再过一个月是姐姐的生辰宴,府上正缺一批做粗活的仆从,买下来,也不算白来一趟。
我单手拎起脏兮兮的小猫兽,抱在怀里搓了把耳朵。
小猫的耳朵趴了趴,半死不活的,似乎刚才蹭过来就花费了全部力气。
把猫塞进篮子里,用赠送的棉布垫子擦了下手。
我抬脚绕开风姿卓越的霖祀,却被他抓住了脚腕。
呵。
「什么脏东西,也敢碰我?」
我狠狠的踹了他一记窝心脚,把人踹的一个仰倒,没愈合的伤口渗出血气。
我嫌弃的甩甩一角,斜了奴隶贩子一眼。
那人弯腰恭敬的送我离开,阴险的三白眼就对上了做作端坐着、面露不可置信之色的蛇兽人,眼神微微暗了下去。
这些手握正规渠道的奴隶贩子们尤其人精,他们不会拦着奴隶自寻出路,也不会有意为难自己的货物。
毕竟身契在自己手上,奴隶们这样做也算一种变相拉客,偶尔还能赚上一笔,因此若合适,也愿意助这些奴隶一臂之力。
蛇兽人的小手段当然都被他们看在眼中。
但拉客不成还招惹大客户不悦的奴隶,总是要吃不少苦头的。
我这一脚,就足够把这家伙的待遇拉到最低一档,吃点苦头了。

3
我回到家里,陷入昏迷的小猫兽在经历了短暂的治疗和清理之后,被重新送回我身边。
他大抵一截小臂长,纯白的毛毛蓬蓬松松,两只耳朵上的尖尖都是很浅的黄色。
我撑着下巴,捻起一块点心,仔细回忆。
我没看错。
前世有只猫兽人凭空出现,为出游的我拦住了一批劫匪。
事后拂袖而去,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样貌,却记得他的耳朵。
猫兽人的耳朵毛色是另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明。
白猫兽很少,只有耳朵尖是浅黄色的自然更加罕见。
真是凄惨,恩人小猫。
我的视线落在他因为伤口治疗被剪得坑坑挖挖的毛,强忍笑意。
「就当还人情了,小丑猫。」
我伸手钩住他的耳尖,毛毛微微颤抖。
不知道是因为疼痛,还是无意识的梦魇,也像是单纯在抗议我说的话。
他一直没醒。
名医被我邀请回来,那白胡子老头儿捋捋胡子,只说是营养不良、身负许多陈年旧伤,新鲜的内伤不少,又有骨头将断不断的,如今好不容易到了安全环境,紧绷的神经一松,就昏睡过去。
以兽人卓绝的自愈能力,很快就会醒,好好养着就行。
用药与否,只决定了他的恢复程度和速度而已。
于是我的身边就多了一只长期沉睡的猫兽,行动坐卧,要么趴在膝头,要么窝在竹篮里,总是带着。
这样的花边消息传的快极,连沉迷事业的父亲都隔了几座山给我发信来八卦。
我没回他。
何况我也没有多想,毕竟曾经是对方有恩与我,治疗也算两清,总不好再套娃似的挟恩图报。
也许霖祀就是这样想,他以为我狭恩图报?
事实上,若他真不愿意,也可以直接拒绝我的。
那是为了什么呢?
我垂下眼,最后的记忆越发清晰,有画面在我脑海里放大,最终定格在我那庶妹的发髻上。
那是一支价格不菲的雕花红玉簪,在她素色衣裙的搭配下,实在突兀。
父亲对叔伯的孩子也好,钱财从不缺他们。
一只簪子没什么大不了,只是不像我那妹妹的风格。
倒像是我曾送霖祀的一块半成品的玉胚子。
哈。
拿我的东西去讨好我的妹妹?真是垃圾。
我冷笑一声,手中的点心化作粉碎,细渣落了沉睡的小猫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