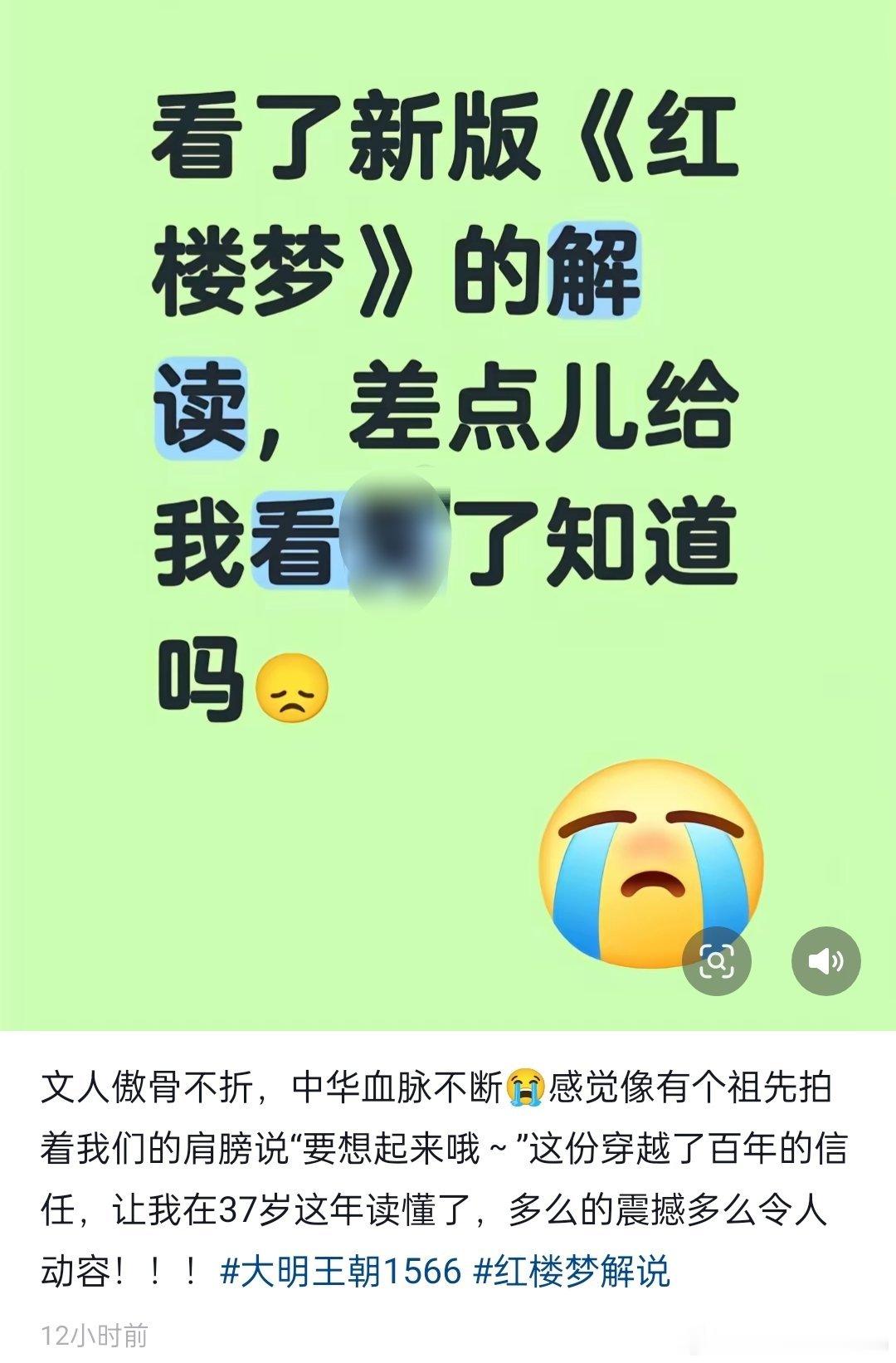1939年8月,豫西大地被盛夏的热浪裹挟。
郏县的空气像一锅煮沸的粥,黏稠而闷热,连蝉鸣都透着一股焦躁,
仿佛天地间绷紧的弦,随时会断裂。
刘子龙蹲在后院的菜窖里,头顶的木板缝隙中漏下几缕昏黄的光,
照在他布满老茧的手指上。

他正将一张薄如蝉翼的纸条塞进墙缝深处——
那是用米汤密写的农会成员名单,墨迹遇火方显,字字如血,藏于无形。
地窖口忽然传来三短两长的轻叩声,节奏清晰,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是刘子龙和谢文甫约定的暗号。
刘子龙心头一紧,肌肉瞬间绷紧。他猛地抓起墙角的铁锨,脚尖一挑,木板“哗啦”掀开。
刺目的阳光倾泻而下,晃得他眯起眼。
一个穿着月白绸衫的男人站在窖口,手里摇着一柄象牙折扇,
扇骨上“壮志凌云”四个篆字在日头下泛着冷光。
锃亮的皮鞋一尘不染,倒映出地窖的幽暗,也映出刘子龙裤脚上未干的泥点。
“子龙兄,别来无恙?”关会潼笑着开口,这小子说话跟抹了油似的,听着就不实诚。
刘子龙的手在铁锨柄上收紧,又缓缓松开。
眼前这人,曾是樊钟秀的司令部参谋,更是樊的亲外甥。
九年前,他们在建国豫军共赴生死,粮尽援绝时,关会潼还分他半块干馍。
临别时,关会潼拍着胸脯说:“到了南京,找我!我定给你谋个前程!”
如今,他回来了,衣冠楚楚,领口别着一枚银光闪闪的军统徽章——
蓝底白日,鹰隼展翅,象征着国民政府最神秘的情报机构。
“关兄,多年不见,你混得风生水起了。”
刘子龙从地窖爬出,拍了拍裤腿的尘土,语气平静,眼底却如深潭。
堂屋里,关会潼的随从已摆上随身带来的酒菜。
一盘烧鸡油光发亮,鸡油滴在青花瓷盘里,凝成暗红的一滩,
像极了战场上未干的血。
关会潼亲自执壶,琥珀色的高粱酒注入玻璃杯,涟漪微漾。
“子龙,”他声音低沉下来,折扇轻摇,却扇不去屋内的沉闷,
“自那年兵败,你我各奔东西。我辗转去了南京,四处靠找朋友投亲友谋求发展,两年后中华民族复兴社(军统的前身,因成员穿蓝色上衣黄色裤子也称蓝衣社)招贤纳士,我就积极报名了。
我本一介军需,无甚大才,但戴老板——戴先生亲见我后,说我‘有胆识、通民情’,
便将我留在身边,参与‘蓝衣社’的早期筹建。”
他眼中闪过一丝追忆,“后来,我随组在南京、上海等地锄奸,亲手处决了七个勾结日寇的汉奸。
戴先生曾拍着我的肩说:‘会潼,你这双手,干净!’”
他顿了顿,语气陡然沉痛:
“可南京沦陷那日,我亲眼看着同胞被驱赶进江边的坑里,机枪扫射……
三百多人,一个没活。我躲在芦苇丛里,血水泡着我的脸……
从那以后,我对日本人,恨入骨髓。我对党国,忠心不二,只为此仇,此恨!”
刘子龙静静听着,指尖微微发凉。
他想起徐州监狱里那些被烟土毁掉的青年,
想起朱鲁岭与日军军官握手的照片——
仇恨,原来不止一种形态。
“我听说你被朱鲁岭陷害,坐了一年牢,出来后拉起队伍,在龙山打土匪保家园。”
关会潼直视着他,眼中竟有几分敬意,“岳站长听说你的事,说你是‘忠勇之士’。
我向他力荐你,说若能得你相助,河南站必如虎添翼。
如今国共合作,枪口一致对外。只要能杀鬼子,便是英雄。”
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烫金委任状,红印赫然:
“只要你点头,立马任命你为军统河南站特别行动组组长,
手下弟兄们的饷银我包了!”
刘子龙的手指在杯沿轻轻摩挲,冰凉的玻璃贴着掌心的老茧,
像在丈量一段无法言说的过往。
他看着关会潼手腕上那块金表——走得比谁都准,可心,却早已偏了轨道。
这提议,是糖,也是刀,裹着“抗日”的外衣,藏着吞并异己的野心。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前的龙形玉佩——
那是董秀芝亲手用红绳系上的。
玉坠贴着心口,温润却发烫,像一块烙铁,烫得他心口生疼。
“军统?”他故意迟疑,声音低沉,
“我听说你们专搞暗杀,不干正事。上个月许昌的共党联络点,不就是你们端的?”
“那是中统刘少甫干的勾当!”关会潼立刻反驳,拍案而起,
金表链“叮”地一声撞在桌角,晃得人眼花,
“听说他还是你洛阳师范的同学。我们军统只打日本人!
锄奸反特,保家卫国,这才是正道!”
窗外的蝉鸣骤然急促,像极了去年在壮丁队时听过的集结号。
刘子龙盯着那枚军统徽章,突然笑了,嘴角咧开,
露出缺了颗门牙的豁口——那是徐州监狱里,被特务用枪托砸的。
“加入可以。”他慢吞吞地说,往嘴里扔了颗花生,壳子咬得“咯吱”响,
“但我有条件:只杀日本人,只杀汉奸。不打内战,不碰共党。枪口,必须对外。”
关会潼的笑容瞬间凝固,金表链“咔”地卡住,
像被无形的手扼住了喉咙:
“子龙兄,这……不合规矩。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现在是国共合作,是兄弟,团结一致打小日本。
当然不会让你对付共产党,可将来的事,谁说得准?”
“要么同意,”刘子龙霍然起身,肩头故意撞翻酒壶。
高粱酒泼洒一地,暗红如血,顺着桌腿蜿蜒而下,
恰巧露出他靴筒里藏的匕首——乌木柄,精钢刃,柄上刻着“护民”二字,
与关会潼腕上的金表形成刺目的对照。
关会潼伸手去扶酒壶时,金表链不慎勾住刘子龙的枪套,
扯开的缝隙里,露出一角鲜红的布料。
两人同时僵住,空气瞬间凝固,蝉鸣都戛然而止。
“要么免谈。”刘子龙猛地抽回手,表链“啪”地弹回关会潼腕上。
空气凝固。蝉声骤歇,仿佛连风都屏住了呼吸。
日影西斜,堂屋的光影由金黄转为暗红。
关会潼终于叹了口气,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好……好!既然你执意如此,那就先以‘外围人员’身份挂名,不入正式编制。
你手下的狩猎队,可以编为‘特别行动队’,归你指挥。
等立了功,我向岳站长保举你。”
他转身欲走,忽又停步,回头说道:
“过几天,我来给你们送经费,你先潜伏到许昌,把中统的刘少甫干掉,他不但贩卖烟土,还私下勾结日寇,出卖军统同僚。
事成之后我在站长面前,为你请功。”
脚步声远去,碾过院中碎石,像碾过人心。
刘子龙立在堂屋门口,望着关会潼远去的背影,绸衫飘动,金表晃眼。
他突然觉得,这局棋,深不见底。
“子龙哥,我们真的要参加军统?老百姓会怎么看我们,今后如何向组织说清楚?”武凤翔忍不住问道。
“加入是暂时的,是潜伏,是自保,也是利用。毕竟,我们现在已经和组织失去联系很久了。”
刘子龙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想不通,我要去延安,汉杰早就去了。”武凤翔掏出手枪递给刘子龙:“老师,相信不久我们还会见面的。”
武凤翔决绝地离开了。刘子龙回到菜窖,重新取出那张密写名单,指尖轻轻抚过每一个名字。
他知道,从今往后,他不能再为他们提供庇护,反而要将他们藏得更深。
可另一面,他又无法忽视——
军统有情报网、有经费、有武器,更有直面日军高层和接触国民党机密的机会。
若能潜伏其中,或许能获取更多机密,救下更多同胞,甚至……为党在敌后布下暗棋。
国难当头,何分左右?只要能抗日,便是正道。
他低头看着地上那滩酒渍,已近干涸,像干涸的血。
风从院外吹来,卷起几缕香灰,袅袅升腾。
香灰看着是土,风一吹,全是火的魂。
他握紧了那枚玉佩,心口滚烫。
这一局,他必须走稳每一步。
为了活着,为了复仇,更为了那束藏在黑暗里的光——
那光,叫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