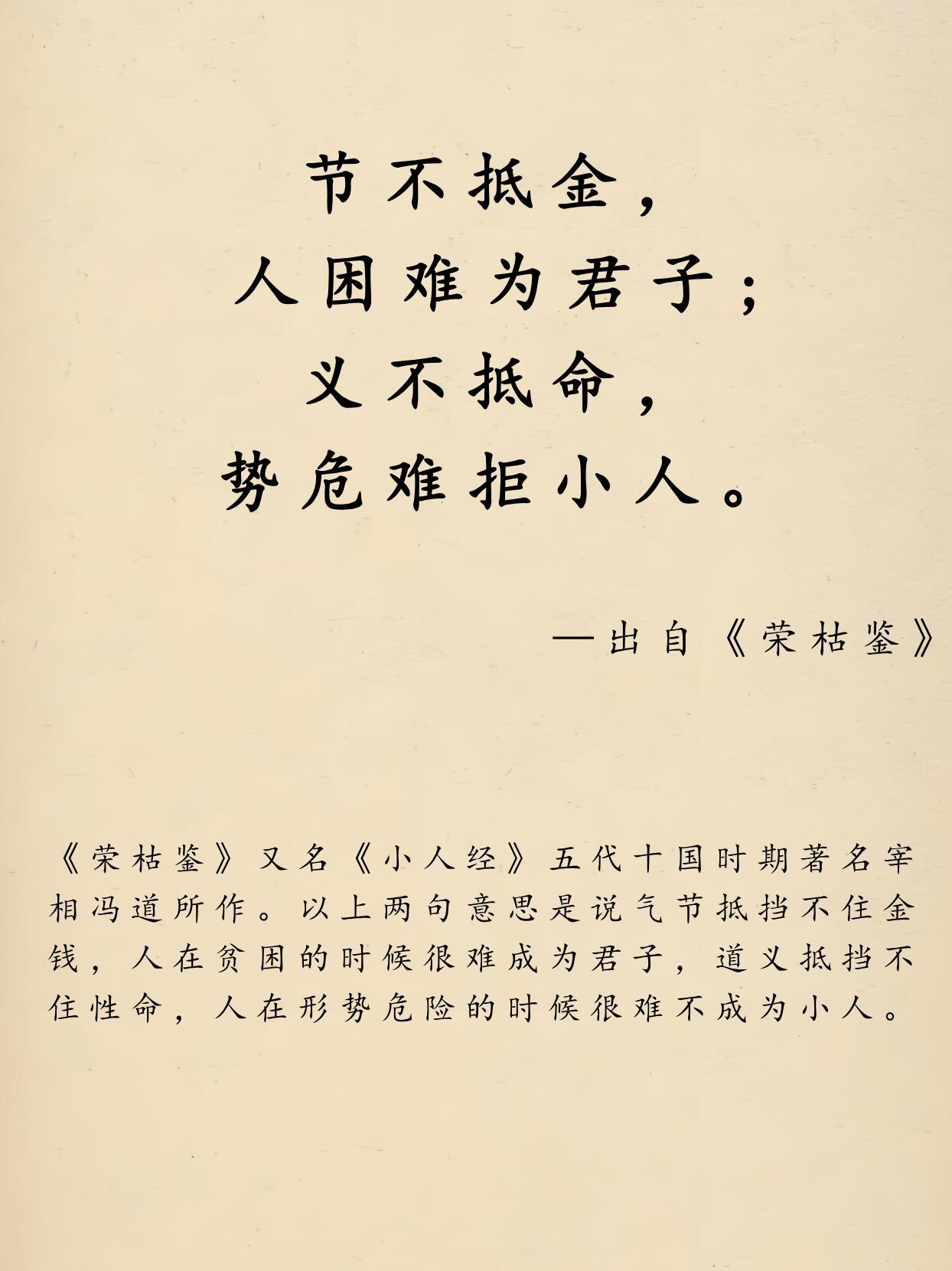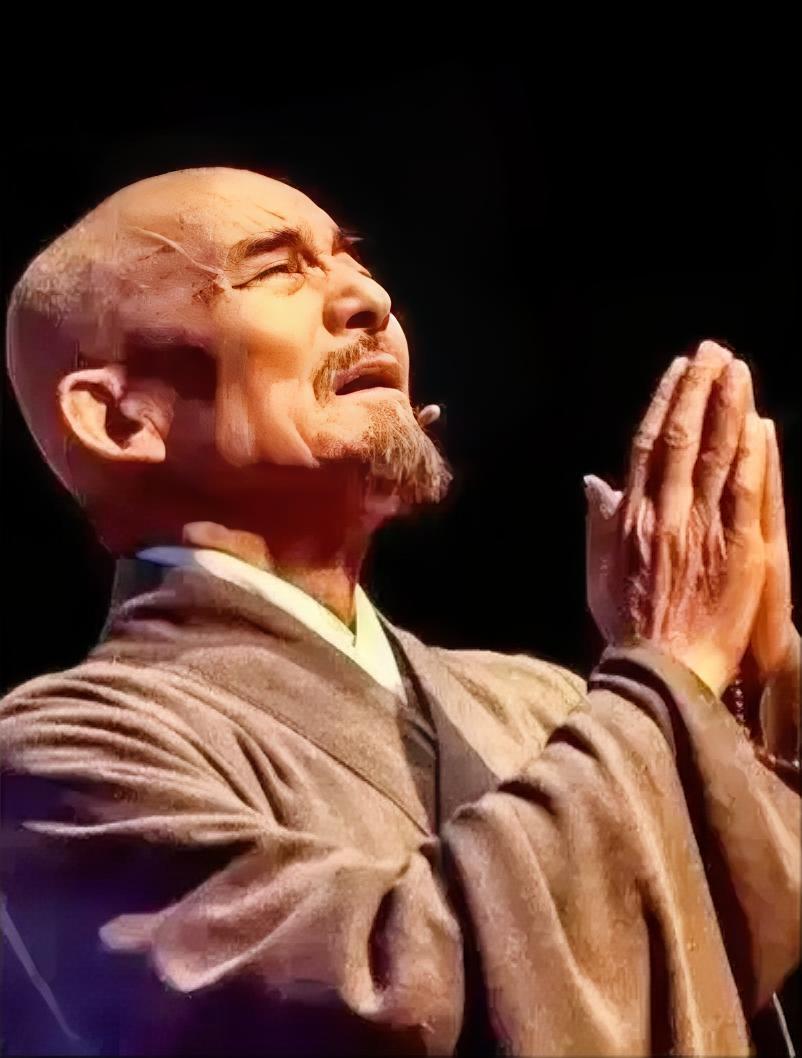作者:黎荔

拆开那方方正正的包裹,一股子沉郁的、混合了松烟的腊香,便猛地扑了出来,不像鲜肉那般活泼泼的腥,是沉下去的,带着时日与烟火的厚重。是湖南的学生,年复一年,捎来的腊肉。一块是烟熏的,油亮的深琥珀色,肉质绵软些,仿佛将一整个冬天火塘边絮絮的夜话,都熏进了肌理;另一块是风干的,赤褐,硬挺,肌理紧实如湘西山地的肌腱,是日头和风刃经年累月雕琢出的劲道。将它们并排放在白瓷盘里,昏黄的厨房灯下,竟有些像两枚古老的印,沉甸甸地,压住了满室流动的时光。
我的湖南学生说,这是她父亲今冬的手艺。我的思绪,便不由地跟着这肉的纹理,溯到了湘西的某处山坳里去。我想象那定是入了冬,山间的风硬了起来,带着清冽的刃,削着人的脸颊。家家户户的窗台、阳台,乃至路旁光秃秃的树干上,便悬起了一排排黑黢黢的物事。那不是静物,是时间的果实,在风里微微地晃,像一排排沉默的、守岁的卫兵。空气里于是终日浮动着一种复杂的香,咸是底子,上面漾着阳光的暖、松枝的烈、还有说不清的草木灰的清气。若是熏烤的人家,屋里必有一个不熄的火塘,红红的炭火映着围坐人的脸,也舔舐着高悬房梁的肉。燃料是上好的硬木,茶树或是杨梅树,偶尔投入松塔、橘皮、谷壳,那烟便带了山林与果实灵魂的幽香,丝丝袅袅,日复一日,夜复一夜,耐心地将那鲜红的肉身,浸润、熏染,镀上一层厚重的、金黄的铠甲。那烟与火,是比阳光更霸道的笔触,将山野的魂魄,一笔一画,都写进了肉质纤维里。
这烟与火,这风与阳,竟让我想起古老书卷里的话来。摊开那部被视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在《噬嗑》卦的彖辞里,赫然有这样一句:“晞于阳而炀于火,曰腊肉。”十个字,把太阳与火盆、时间与风、人与兽,一并钉在卦象里。说得何等简洁,又何等透彻!曝晒于太阳之下,烘烤于火焰之上,便叫做腊肉。八个字,一部食物的史诗,一种生存的智慧,便凝在里面了。
我疑心那“晞”字是象声词:肉里残血被阳光抽走时,发出极细的“晞——”,像琴弦被风拨了一下,余韵至今未绝。
《易经》成书于西周初年,那是一个钟鼎彝器上镌刻着神秘纹样的时代,是巫祝的吟唱与青铜的冷光交织的时代。我们的先民,在那样一个宏阔而艰难的年月里,望着分食后剩余的猎物,忧虑着它即将到来的腐坏,便抬头看见了太阳,低头触到了火种。于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开始了:他们将鲜肉高悬,让干烈的北风与温暖的日光,合力抽去丰沛的水分;接着,又将其移至烟火之上,让那些燃烧的松枝、果木的魂灵,化为细密的守护,沁入肌理,抵御漫长光阴里霉菌与蠹虫无声的侵伐。这哪里是简单的食物制备?这分明是一场以岁月为柴薪的、静默的祭祀。阳光曝其外,烈火煨其内,风霜淬其表,人间的温情与耐心注其魂。腊味的诞生,起初并非为了口腹之奢,而是生存之需,是文明在漫长冬季里,为自己储备的一缕带着咸香的“未来”。
想到此处,那案上琥珀赤赭的两块腊肉,在我眼中忽然不同了。它们不再是简单的馈赠,而成了穿过三千年烟雨风霜,抵达我面前的一件文明的“信物”。而将这信物与师生情谊绾合在一起的,是另一位著名的古人——孔子。
《论语·述而篇》那句熟悉的话,跳将出来:“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脩,便是干肉;束脩,一束十条。历来的注疏家,多将此解释为孔子设定的微薄门槛,以示其“有教无类”的胸怀。然而对着这腊肉,我忽然对这句话有了别样的体味。那个遥远的春秋时代,一个布衣少年,或许来自穷困的野鄙,他怀着向学之心,要去拜见那位名动天下的夫子。他能拿出什么呢?金银珠玉是没有的,或许只有母亲连夜熏制好的一束干肉,用干净的茅草捆扎得整整齐齐。这肉,可能也经历过“晞于阳而炀于火”的过程,带着他家屋檐下阳光与烟火的气息。他捧着这束肉,走过尘土飞扬的道路,心中满是忐忑与恭敬。
这被阳光与烈火锻造过的肉,这凝聚了风霜与心意的物,便已不是简单的“肉”。它是“礼”,是“贽”,是一个青年迈向知识殿堂时,所能捧出的、最郑重的心意。而那位在洙泗之间弦歌不辍的夫子,郑重地接过这束带着体温的、沉甸甸的干肉时,他所看到的,难道仅仅是“学费”么?他所慨然应允的,是那“自行”而来的向学之心,是对知识与德行的怀敬持诚,是一个家庭将其最珍贵的储藏——既是食物的,也是希望的——托付于他的那份信任。那是一种朴素的契约,以物质为凭证,交换的却是无价的精神薪火。

我的思绪猛地从洙泗之滨被拉回。电饭煲的蒸汽“嗤嗤”地响着,白雾袅袅。我照着学生说的方法,将腊肉切成均匀的薄片,肉是好看的,肥处透明如黄玉,瘦处殷红似赤檀。码在白瓷碗里,淋上几滴麻油,那油便沿着肉的边缘,缓缓地、亮晶晶地晕开。电饭煲蒸米饭时,将这碗腊肉置于蒸笼上。电饭锅低低地哼着,水汽在密闭的空间里,温柔地逼迫着。渐渐的,一丝极其霸道的、油润的咸香,便不管不顾地钻了出来,先是丝丝缕缕,继而浓郁得化不开,充满了整个厨房。这香气是有形状的,像一只无形的手,攫住人的嗅觉,再轻轻一牵,便将人的神魂,牵回了那片土地的深冬里去。
那香气是霸道的,有烟火的厚,有脂肪的润,有盐霜的咸鲜,还有一种经时间陈酿后特有的、近乎醇酒的复杂韵味。待到饭熟肉烂,揭开锅盖,一团滚热的白雾轰然腾起,待雾气散尽,那碗中的腊肉,已是脱胎换骨。腊肉的边缘已变得透明,分泌出晶亮的油脂,肥肉部分晶莹剔透,微微颤抖着,如半融的琥珀;瘦肉则深深吸饱了水汽与油脂,变得深褐、酥软。碗底汪着一层清亮金黄的油。夹一些学生一同捎来的、自家制的豆瓣酱,无须其他菜肴,只将这一碗肉酱与白米饭拌匀。米粒油润光亮,每一颗都裹挟着腊肉的魂与豆瓣酱的魄。送入口中,一种扎实的、澎湃的香,便在舌齿间轰然炸开。那味道,是山野的,是岁月的,是火的记忆,也是阳光的沉淀。
我吃着这碗饭,忽然间全明白了。我那远在湖南的学生,年年寄腊肉,从未提请托,每次只是朴素地说:“老师,这是家里做的,您尝尝。”她也许无意中承袭了最古老的礼数——以食传情,以味载敬。腊肉虽非金玉,却是她家火塘上熏了一冬的心意;不是束帛,却是她父亲手挂于檐下的牵挂。这份“束脩”,带着灶火的温度、山风的凛冽、节气的节奏,以及一个普通人对知识与师长最朴素的敬重。
这“束脩”之礼,形式从十条干肉变作几块湘西腊肉,道路从尘土飞扬的官道变作穿山越岭的快递车,但那内核从未改变:那是对授业者的感激,是对文明的向往,是以最诚挚的“物质之礼”,传递最纯净的“精神之敬”。文明的链环,有时并不依靠煌煌巨著,反而就系在这些寻常的、带着烟火气的物事上,一代一代,薪火相传,滋味悠长。今人多言师道式微,礼崩乐坏。然我每每收到这包腊肉,便知古风未绝。穿过三千年的日月山川,穿过古圣先贤的文献典册,这一缕咸香,不止飘在饭桌上,更飘在人心深处。